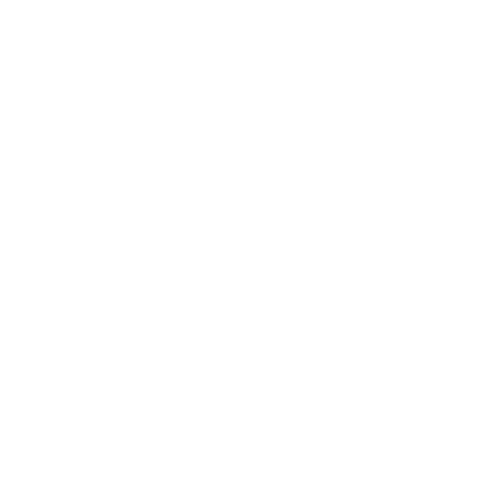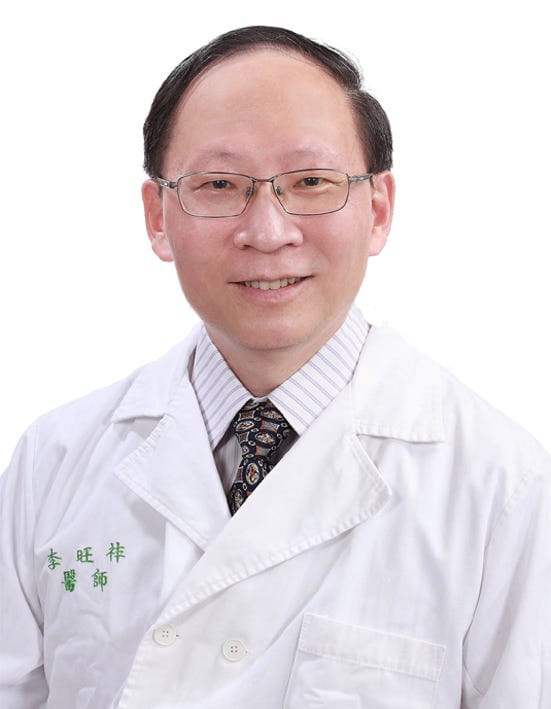隱喻與凝視:愛滋病去汙名化零歧視工作坊紀實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十九刊 (後疫情)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十九刊 (後疫情)
撰稿:b10 廖彦宥
「起初,腐敗、衰亡、汙染、失序、脆弱等引發深層恐懼的元素都與疾病畫上等號。疾病本身成了一種隱喻。接著,只要引疾病之名,以疾病作為隱喻,那股恐懼就加諸在其他事物上了。」
摘錄自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
在愛滋病被發現後的數十年間,愛滋病的治療已經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受到妥善治療的愛滋病病毒 (HIV) 感染者,其日常生活也已經與社會大眾無異,平均餘命也與一般人相差無幾。然而,在社會結構與歷史文化脈絡的影響下,愛滋病仍然被視作可怕的瘟疫,被附著上許多不該屬於它的標籤。這些標籤,使得感染者成為社會的邊緣。他們被迫緘默以對,以免受到醫療照護系統的選擇性排除…
這場愛滋去汙名化零歧視講師培訓工作坊由Virology Education主辦,並由台大醫學系系學會國事部與台灣愛滋病學會協辦。開場嘉賓有Virology Education總監Mark Nelson、系主任盛望徽醫師及成功大學醫學院副院長柯乃熒教授。本次工作坊旨在提供各類醫護人員進行愛滋病去汙名化的教育培訓,邀請本院師生及全國醫學生聯合會性健康推廣部參加。Virology Education是一個推進愛滋病等傳染病的研究、治療與衛生教育的國際性組織,透過在全球各地開辦講座與研討會,使醫護人員協助獲得最新的研究進展與醫療指引,並開展如愛滋病等傳染病的去汙名化工作。
活動不只邀請在愛滋病感染照護場域的工作者們提供經驗與現狀闡述,也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現身說法,講述其在求診期間所受到的系統性歧視。透過這些講演與分享,期望能使得與會者能反思台灣醫療照護系統對於愛滋病之迷思,並且交換想法,以期能在醫療場域內促進愛滋病之零歧視與去汙名化。

愛滋病之歷史與我國現狀
1981年,愛滋病首次出現在世人的面前;兩年後,科學家逐漸了解愛滋病背後的機轉,並開始尋求治療方法。然而,誰能知道,整個社會需要數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使愛滋病的污名化與群眾的恐慌開始逐漸褪除。奇美醫院的杜漢祥主治醫師說,愛滋病的治療已經日益進步,從過去何大一博士研發高效能抗反轉錄病毒治療(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俗稱雞尾酒療法)後經過不斷研究發展,目前只要透過每日服藥,基本上就可以得到控制,甚至未來也有邁向完全治癒的可能。但,「如果愛滋病是可以被治癒的,那麼社會大眾對於愛滋病的認知就能逐漸改觀?」關於感染者和伴侶進行性行為是否會感染的隱憂,杜醫師說,只要感染者血液中檢測不到病毒,就不會對他人造成血體液傳染,即Undetectable=Untransmittable,U=U。「這對於我們過去受的醫學訓練,對於大部分案例都認為有例外的人來說是個很大膽地宣稱,但這就是事實。」感染者只要經過良好的控制,並且搭配預防性的配套措施,如暴露前後的預防性投藥、母子垂直感染預防措施,是可以和伴侶進行性行為,並可以生出無HIV感染的小孩。
而隨著台灣在愛滋病治療與與預防的逐漸成熟,愛滋病的每年通報病例數也逐年下降,而在治療成果方面,也獲得很好的進展。杜醫師說,台灣已經達到90–94–95,也就是有90%的個案知曉自身被感染,且其中94%的人也正在規律服藥中,服藥中的感染者有95%偵測不到病毒。這相較於國際上在2030年的願景95–95–95已經相差無幾,能預期在未來數年後台灣便能達成。而在達成後,面對感染者的老年的長期照護以及器官逐漸老化造成的慢性病叢生,便成為HIV照護的下一個課題。杜醫師說,「這不只需要感染科的努力,同時還需要醫院各科的整合才能實踐。」因此,第四個95,即有95%的高齡感染者能得到妥善照護也是台灣需要努力推動的目標。
國內的治療發展縱然已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對於愛滋病的異樣眼光仍然潛藏於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根據杜醫師的統計,仍然有35%的醫療場域工作者在其工作中耳聞過對於感染者的歧視性言論,可見台灣社會對於愛滋病的態度依然有疑懼與誤解。在這樣的環境下,HIV感染者受到拒診等不平等的待遇,只能隱忍病痛,甚至不敢向醫院告知自己得病的事實。社會結構與歷史文化的汙名化,使得感染者對於自己得到HIV感染的認知視作一場不可挽回的悲劇。
而對於有些感染者即使接受治療,卻仍然測得到病毒的問題,杜醫師表示這也有可能是人生的際遇所導致的,例如剛被感染、當兵、失業甚至是失戀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得這些帶原者無法按時服藥,使得其病毒量在血液中仍測得到。對於這些病人,杜醫師認為需要透過適當的醫療介入措施,那麼這些感染者的醫療仍然能夠獲得保障。
「一個專業的醫護人員也無法為我減緩痛苦,那我還應該相信誰?」,杜醫師說。而在疫情肆虐之際,HIV感染者也遇到領藥與接受治療的困難,當醫療量能被全心投入於抗擊疫情之際,HIV感染者的權益便受到忽視,這同時也是資源分配和教育的問題,需要社會各方的通力協作。杜醫師也推動了他所在的醫院內的愛滋病宣導計畫 — 奇美友愛,透過各科醫師、主任與院長的演說推廣,希望能讓社會大眾對於感染者的恐懼能夠逐漸消弭。
臨床現場的愛滋病患者就醫群像
「台灣社會雖然對於愛滋病的看法已經有明顯的變化,但對於感染者的歧視卻仍然存在。」,愛滋病帶原至今已經十四年的黃義筌先生說。作為親身經歷者,他向與會者娓娓道出自身與感染者朋友們在醫療場域下所遇到的拒診等歧視性待遇,使我們反思現今醫療系統對於HIV感染者的結構性歧視。
首先是一位愛滋病友在二十五年前遭遇的案例,那時的法律尚未對於醫師拒診而有懲罰。在一次旅遊中,他因為得到急性䦨尾炎而去看診。然而在就診時,因為他說出他有HIV感染,而被護理師用黃色警戒線將他與他的朋友團團圍住。「這是為了保護你們,也是為了保護我們。」,那位護理師說。而後續他的䦨尾炎也沒有得到開刀處理,只有得到一包消炎藥。這樣類似劇情一連重複了五次,來回奔波之下只有五包消炎藥、疲憊的心靈和抱恙的身體。直到最後一次,他的朋友決定用誇張的方式哭喊著,並隱藏HIV感染者的事實,才使醫院願意為他開刀。而這位感染者在開完刀一醒來的想法卻是愧疚的,因為他沒有向醫院告知自己是愛滋帶原這件事。「如果我們都要透過隱匿自己是HIV感染者才能獲得妥善的醫療,那會有人願意向醫院告知實情嗎?」
然而,在修法過後,拒診是否就不再發生?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恐懼仍然植根於人們心裡幽微的深處。另外一個案例則是黃先生五年前的牙醫看診經歷。長期飽受牙齦出血的他決定去洗牙,但當他就診,牙醫助理插入健保卡的那一刻,卻又被以各種理由推託,例如本日排程已滿、沒有適合您的情況的設備等等。這使他懷疑自己的健保卡上面的就診紀錄是讓牙醫拒診的原因之一,無可奈何之下,他只能反覆找尋,在第五間終於有願意為他洗牙的醫師。即使他的病情已經控制得很好且沒有傳染風險,但醫療照護系統卻仍然保持戒心,並視作是麻煩的事。
有上述經驗之後,他之後都到聯合醫院昆明分院進行愛滋特約牙醫治療。雖然在這裡HIV感染者不用擔心被各種理由拒診,但對黃先生來說仍然是一大不便。「如果我要搬遷到其他地方時,那我的就醫保障可能就又消失了。」黃先生總結出就醫療負面經驗對於愛滋病社群的影響,包括(1)影響就醫意願;(2)延誤就醫,錯失診療機會;(3)醫療資源不平等;(4)降低告知意願。因此,他也希望在未來,能有對於HIV感染者更為友善的醫療場域,使得感染者社群的醫療能得到保障。
醫療場域的愛滋隱性歧視作為
HIV感染者對於醫療體系就有如例外狀況,醫護人員對於感染者的處理不甚熟悉,便使得感染者受到各式各樣的隱形歧視。在臺大醫院擔任愛滋病個案管理師的陳伶雅首先向與會者拋出兩個問題:誰看起來像愛滋病感染者,又有哪些病人應該接受愛滋病的檢驗?這兩個問題分別對應到台灣社會對於愛滋病患者的迷思以及醫療體系中出現的愛滋病部分群體延遲診斷的情形。
對於台灣的愛滋病延遲診斷問題,陳個案管理師指出台灣的延遲診斷發生在這三大族群:五十歲以上大於百分之六十、異性戀者百分之五十八、女性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被延遲診察出愛滋病。因為這些群體的特性與大眾對於男同性戀較容易得到愛滋病的刻板印象不同,使得他們認為自己不會被愛滋病所傳染。然而,愛滋病帶原者是多樣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們都可能因為意外而被感染愛滋,但總是被社會選擇性地忽視。而對於醫護人員,除感染科可能會對於病患的免疫不全症狀多加注意,並且對其進行全套的免疫不全檢查之外,其他科別要觀察到該名患者有愛滋病的機率更加微小,而這也這使得這些群體成為愛滋病傳染防治的破口。
而醫療體系對於HIV感染者的迷思,例如病人應直接主動告知有愛滋病,醫療人員才來得及做血液傳染措施防護、發現病人有血液傳染,一律戴雙層手套和隔離衣…等等,都使得這些戮力將自身的病狀控制到最佳狀態,鼓起勇氣直面愛滋病與社會大眾的帶原者感到無力。醫護人員對正常情況下的醫療寬鬆以待,甚至有些不經意,而面對愛滋病帶原者,由於他們需要在常規之外需要被謹慎看待,反而對於醫療常規皆步步遵守,甚至對其進行過當的消毒措施,著實諷刺。
而在後疫情的情形下,因為愛滋病帶原者需要定期服藥,所以需要定期到醫院回診。然而,在疫情的情況下,人流管控使這樣的流程變得無法進行。此外,插入健保卡的行為也對愛滋病帶原者擔憂是否會使得自己的隱私外洩,這更使得愛滋病帶原者怯步,而無法正常調控自身的病情。而這時候,個案管理師便顯得十分重要,因為其可以疏通各個醫療窗口,整合提供感染者合適的就醫管道。
另一位講者,聯合醫院昆明院區的愛滋特約牙醫師曾禹璇則提到一位牙醫學生在自己大三發現自己得到愛滋病的故事。他在學校受到系統性的歧視,並且差點被退學 — 因為人總是不知道要如何處理自己未知的事物,尤其是保守的牙科。所幸,這位牙醫學生撐了過來,進入實習,但他仍然被要求只能碰觸愛滋帶原的病患,正常的病患他無法治療,而這些政策導致他的受教權及實習權益受到侵害。
而受到社會的歧視之下,這些愛滋病帶原者也因此產生一些心理壓力。曾醫師便講述她曾經看過的愛滋病帶原者,為了自己能看病而在健保卡寫下的文字:「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是愛滋病帶原者,請辛苦的醫護人員一定要做好防護措施!」這種卑微的請求態度,同時也是社會對於愛滋病患者不友善的寫照,許多受到社會排擠愛滋病帶原者聽聞醫師向她詢問病情便衝出門外、或是連忙否認、或是歇斯底里。「雖然根據我的研究,有五成的牙醫師願意看診愛滋病患,但實際狀況只有愛滋病患者實際走訪才能證實。」曾醫師說。「醫師甚至需要一些面對揭露自身愛滋病情的患者伴隨而來的情緒創傷狀況的知識,並給予支持和鼓勵。」
愛滋病的汙名化,使得正確的衛教訊息無法正確傳遞、對於愛滋病的潛在帶原者也不敢接受篩檢,在篩檢後也無法有效提升其治療意願,最後反而會增加愛滋病在防治上的困難。於是乎,恐懼最終成為恐懼的來源,而唯有愛滋病的去汙名化才能擺脫這種惡性循環。
醫者,人也:何大一的故事

在閉幕時,主辦這次活動Virology Education的台灣區副總監,成功大學醫學院副院長柯乃熒分享了一則她和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發明人何大一醫師的故事。在當年愛滋病剛進入台灣,社會對其普遍充滿恐懼和誤解,而何大一醫師因為他台裔的身分,想要把雞尾酒療法引入台灣,造福台灣的病友。他在全台巡迴演講途中,那時的柯院長接到許多HIV感染者的請託,想要見上何大一醫師一面,而何醫師也爽快地答應了。他直接在他下榻的飯店直接診視那些感染者,並且觸摸他們的身體 — 這是在那時台灣社會中所畏懼的,但何醫師卻不害怕,並溫柔地給予支持,讓這些病友們重新燃起希望。而醫生便是這樣的角色,陪伴、支持、並給予希望。希冀透過對於醫界新生代的宣導,能夠從這一代開始,彌除醫護人員對於HIV感染者的異樣眼光,並提供一個感覺安全,隱私受保護的空間,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整理記錄:系學會文刊部 B10 廖彦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