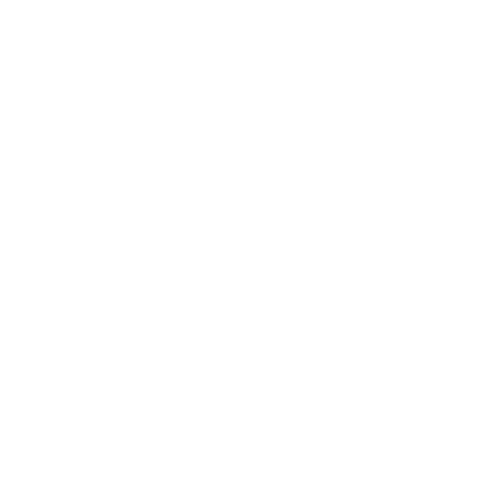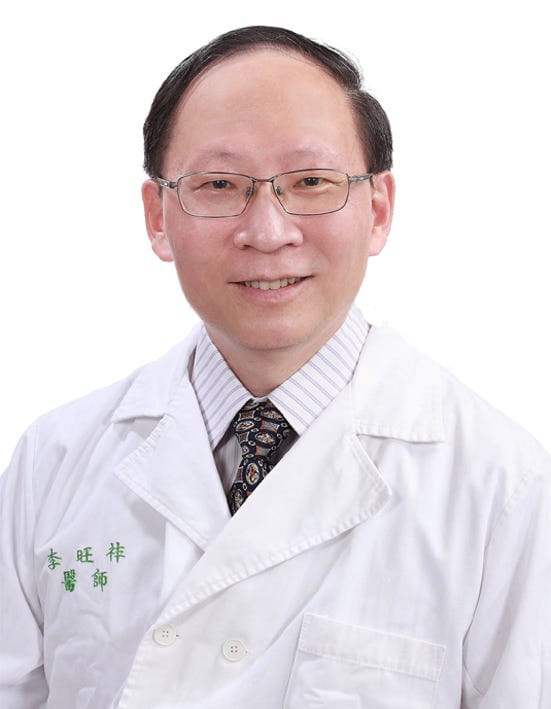解剖歷史:台大解剖學科與體質人類學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二十刊(見證)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二十刊(見證)
受訪:盧國賢 教授 (台大醫學院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科)
撰稿、訪談:b10 廖彦宥

盧國賢教授是台大醫學院解剖學科退休的名譽教授,在四十餘年的教學生涯中歷任解剖學科主任、學務分處主任、國家考試委員等職位,可謂作育英才無數。盧教授在解剖學科中所經歷的人事物,也成為我們見證解剖學科發展的活化石,讓我們得以一窺解剖學科肇建時期的樣貌以及在戰後的發展。台大解剖學科的一大特色便是體質人類學研究,而盧教授便承繼余錦泉教授、蔡錫圭教授的風範,後來也在其電子顯微鏡的本業之外對於體質人類學研究、醫學人文與醫學教育亦有所貢獻。
台大醫學院的「體質人類學研究」發展
在日治時期,日本人為了統治與殖民的需要,日本人對於台灣在地的族群進行許多研究,而體質人類學也不例外。隨著高等教育在台灣的成立,作為台大醫學院的前身的總督府醫學校成為台灣體質人類學研究的濫觴,開始收集許多本島人的骨骼進行研究,並且對其族群進行區分,如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等。這些研究對於族群的分類、民生用品的尺寸及生產都十分重要。在台北醫專時期,眼科教授宮原敦便在墾丁寮遺址發掘了許多時前時代的文物與骨骼,並於1936年交由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解剖學教室保存。此外,隨著日本的軍隊征伐與南進政策等影響,也收集了諸如海南人等其他地區的族群的骨骼進行研究。
終戰後,台灣的體質人類學研究變得頗為分散,從中央研究院的安陽殷墟頭骨與國防醫學院體系都有在研究;而台大醫學院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則與日本方面一直有在交流。在盧教授的回憶裡,曾有多位研究者在台大做體質人類學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後,就到日本去進修。然而,戰後台灣隨著公民意識的喚起,對於遺骨的挖掘的限制逐漸增多,使得實驗素材日益稀少之外,國際學術界也逐漸轉向其他方向,這方面的研究也逐漸乏人問津。而隨著國外有關體質人類學技術日新月異,如台大醫學院的體質人類學還是用傳統方式測量,但在現在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大多是使用電腦儀器去測量,並且也隨著基因體相關技術的逐漸成熟,體質人類學逐漸開始往其他方向,如分子生物學、遺傳學的層面發展。在種種環境因素下,台大醫學院體質人類學研究因而在缺乏資源與人力的支援,推展體質人類學研究逐漸停下腳步。如今,這些當年的研究資產都收藏於蔡錫圭教授所創設的台大體質人類學研究室內,等待著後進的到來。
台大醫學院解剖學科人物群像
在總督府醫學校至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時期,解剖學教室(台大醫學院解剖學科)的兩位重要人物非金關丈夫與森於菟兩人莫屬,兩個人分別扛起了解剖學科中大體解剖與組織學的兩個重要分類。終戰後,他們也都在改制後的臺灣大學醫學院擔任教學數年後才歸國,使得戰後百廢待興之際的台大醫學院解剖學科得以完善地交棒給後來的余錦泉教授與蔡錫圭教授。金關丈夫教授是台灣體質人類學的重要人物。他在台灣的研究期間取得了許多成果,至今仍保存在台大醫學院體質人類學研究室內。金關教授的解剖學課堂深受歡迎,他以粉筆繪圖輔助清晰的講解,贏得了當時醫學生的好評。據說他的考試也很生活化,常以日常動作入題,例如彎腰撿起物體時所需使用的肌肉與神經通路等方式。除了體質人類學研究,金關教授還對臺灣手工藝品的創作和收集有深入研究,曾與台灣藝術家顏水龍等人有過交流。回到日本後,金關教授在日本體質人類學研究中也佔據重要地位,對日本族群的源流和發展有獨特見解。過世之後,金關教授與其父親也將自身的骨骼捐贈與其母校九州大學,可謂是將一生都奉獻於解剖學之中。

森於菟教授則主要是在組織學、形態發生學等相關研究見長,對於台灣各族群的皮膚、掌紋與毛髮色調的調查研究,以及台灣兩棲類動物的外形發生等等,均有卓越之成就。或許是受到其日本陸軍衛生總監,同時也是文學家的父親森鷗外的影響,他的教學方式據說較為嚴謹,幾堂課下來從他的板書抄錄下來的內容已經能累積為可觀的數量了。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森教授臨危受命擔任醫學部長一職,並且指揮師生疏散至桃園的大溪小學校,歷經數次的徒步跋涉歷經艱辛才得以完成。兵馬倥傯之際,森教授將所有的醫學研究設備、文件與書籍藏於台北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在士林的防空隧道內,才使得這些文獻得以倖免於數月後的台北大空襲中。森於菟在戰後返日後,其最為牽掛的即為其於慌忙之際未能一併帶走的他的父親森 鷗外的遺物,這些遺物在後來由蔡錫圭教授保管,並經過數年的努力,終於在1953年將其還回森教授的手中。
余錦泉教授是個很嚴謹的人,在他的書桌的擺設總是格局方正,書桌上的鋼筆、手錶排列的整整齊齊。余教授的書櫃有個特色,他會在所有排列在書櫃上的書畫一條直線,要將書放回的時候,只要將直線對齊就可以放回原位。當有人沒有按照直線對齊放回時,他就立刻查出借書未正確歸位者。而下班時,他總會在辦公室門前駐足數分鐘,確認一切都就緒後、才舉步返家。余教授在戰後許多日籍教授皆回到日本之際,作為唯一的台灣人,擔下了重建解剖學科的重責大任,在他擔任解剖學科主任期間成立碩士班以培養後進,對人員、設備、教學也歷經許多探索而得以有許多進步。此外,面對戰後如台北醫學院、高雄醫學院等私立醫學院的興起,余教授也多次派遣專業人員前往協助,為各醫學院的解剖學科奠定基礎,絕對可以說是台灣戰後解剖學教育的肇建者。在嚴謹之餘,教授也是十分幽默,盧教授回憶八零年代,那時的他總是留著長髮,算是在當時比較叛逆的髮型,而教官看到是教授也不能多說什麼。余教授看到盧教授他那髮型,便打趣地說:「你按呢剃頭店是欲做啥物生理?(台語,即『你這樣理髮店還做什麼生意?』)」,盧教授回憶起這段往事,不莞爾笑了出來。
盧教授也提到,當時日本作為醫學較為發達的地區,許多大陸人士也會赴日本進修研習。例如戰後來台的葉曙教授[1],他奠定台大病理學科的基礎,並協助推展病理解剖和檢驗的概念到全台灣各私立醫學院、公私立醫院。在戰後初期,台灣的醫學教育僅有台大與國防兩校。前者較為本土、偏向民間,且以德文和日文為教授所使用的語言;後者則為軍方背景,多為戰後遷台人士,以中文與英文教授課程。在戰後的台灣,醫學教育經歷了不小的磨合過程,因為在日治時期台灣已建立了以德國、日本為基礎的醫學教育體系[2]。當時的台大醫學院多以德文與日文授課,使教授們對這兩種語言十分熟稔。盧教授回憶在讀碩士時,德文必修兩年,他的指導教授陳以理曾給他一份與他研究主題相關的綜述德文文獻,雖已接受英美醫學體系,仍需努力讀完。盧教授回憶起他在台大醫學院的碩士口試時,是由國防醫學院的生物形態學系(即現今之解剖學科)主任梁序穆教授為召集人。
蔡錫圭教授是戰後回台的台灣人,他是終戰前在青島(以德日語為主)完成學業,所以他在當時在台灣大學醫學院的交流溝通並沒有受到太多阻礙。有一次,盧教授在與蔡教授聚餐時,曾經說到要祝他這位老前輩「食百二(tsia̍h pah-jī,台語活到一百二十歲之意)」,蔡教授先是嫌一百二十歲未免太長,但隨後又風趣的補充到「活到一百一十九歲就好」,可見蔡教授風趣的一面。盧教授回憶,蔡教授在九二高齡時,仍然精神矍鑠,還能到肯亞遊覽野生風光。蔡教授也是重情之人,他的研究室裡擺著夫人的骨灰多年;蔡教授對於曾經的恩師也是十分感念,在1969年也曾經到鳥取大學解剖學科從事研究交流,當時的主任正是他在就讀青島醫學院時期的恩師伊藤光三。蔡教授對於台灣解剖學教育的貢獻之一是大體解剖學教材資源的整合,他與國防醫學院的鄭尚武教授一同創建了「台北市各醫學院遺體分配聯絡中心」,使得各大醫學院的大體老師終於不再匱乏,造福許多醫學後進。在1997年,蔡教授將台大醫學院創校以來的體質人類學成果再次梳理,並且同琉球大學學者石田肇教授與土肥直美教授一同進行了骨骼的整理與保存工作。三年後,在謝博生院長的支持下,蔡教授將這些成果收藏於新成立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室」中,並且在往後數年與日本學者一同發表數篇論文。蔡教授也是盧教授開始研究體質人類學的引路人,有感於自己所學及骨骼標本必須有人傳承,於是便讓盧教授跟著一起研究。
林槐三教授與盧教授間師生兼同事的情誼可謂是最深的,林教授曾經受到金關教授與森 教授的薰陶,進行體質人類學與組織學的研究;戰後,森教授的組織學教學則由林教授繼續傳承。此後數年,林教授也出國深造,在九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受政府資助前往美國德州大學進修。他的主要研究分野是電子顯微影像的研究,尤其是有關松果腺的顯微構造。他的治學方式嚴謹,一絲不苟,在沒有十分肯定正確之前,絕不輕易發表。林教授曾經說過,一個細胞大約是數十微米,但組織學切片厚度不過幾微米,電子顯微鏡切片厚片則僅是數十奈米,因此就算看到許多特別的結果也不要太急著高興,反而是要小心地求證,重複實驗得到穩定的現象後再進行下一步的研究。個人亦深受其影響,尤其是在電子顯微鏡方面的研究態度。在實驗或儀器操作上,若有任何不妥,立即嚴加指正。盧教授回憶過去曾經在解剖所剛剛肇建,攻讀第二屆的碩士時,他的第一屆學長不小心碰到了實驗溫箱的一個旋鈕,就直接被林教授不留情面的批評。盧教授也回憶他剛學成歸國在解剖學科授課時,林教授就會坐在教授後面聽取盧教授的教授內容,並且在課後給予盧教授建議。有一次,在講授淋巴結與胸腺的組織學時,盧教授只花了四十分鐘的上完了,但林教授就直接上台進行補充,並且在課後跟盧教授說還有哪些可以補充,哪些部分用其他方式教學會使教學更為順暢讓學生更好吸收等等的知識。林教授在教學與研究的嚴謹態度至今仍深刻影響盧教授。
鄭聰明教授是台大醫學院神經解剖學的發展者,在鹿兒島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後有授政府資助前往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學習神經解剖學。鄭教授平時為人幽默、急公好義、樂於助人,精於繪畫和攝影。上課時邊講學邊繪圖,信手拈來,維妙維肖,對於神經解剖學的教學,常以各種巧妙的比喻來說明,甚受學生歡迎。盧教授說,解剖學還是要會畫圖與攝影,但有些圖似乎還是學不來的,「他畫mastoid process與中耳與內耳的構造,畫得唯妙唯肖,我怎麼畫都還是覺得比例不對。」此外,鄭教授對於攝影上的熱愛,也使許多台大醫學院改建之前的舊照片得以保存。 值得一提的是鄭聽明教授的尊翁(鄭傳對教授,任職於高雄醫學大學)及他的公子(鄭授德教授,任職於長庚大學醫學院)都是解剖學教授,祖孫三代均為解剖學者,奉獻台灣解剖學教育,是解剖學界的佳話。
關於醫學人文與醫學教育
關於醫學教育,盧教授認為身教對於醫學生的養成是重要的,雖然現在的知識取得已經較過去容易很多,但仍然無法取代實際的講課與實習。透過教授對醫學生的親臨指導,使得醫學生得以獲取許多在課本中難以取得的知識與操作技巧。對於盧教授而言,醫學人文中的一部分便展示在這些身傳言教中。另外,盧教授認為,醫學人文的視野不應僅限於西方,我們也應該觀察在東方世界中的醫學史,而在台灣,無論是日治時期及終戰後的醫學發展史,也同樣造就了不同的醫學人文。而關於海外留學的選擇,他以自身在英國的海外留學經歷為例,勉勵醫學生可以去外面看一看,畢竟紙上覺來終覺淺,不如親自經歷,與西方醫學的經典人物面對面。
註:
[1] 日本千葉醫科大學畢業,終戰後任台大病理科首位主任。其著作《病理三十三年》、《閒話台大四十四年》,是台灣醫界傳記文學的經典文學,記錄了台灣病理學發展的辛酸苦辣以及台大早期人事物的生活點滴回憶,可說是台灣醫學珍貴的史料。
[2] 編按:有關此部分,可以進一步閱讀葉永文(2018)。台灣醫學教育的轉型:從日治時期到1950年代。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5),1–30,此處不做進一步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