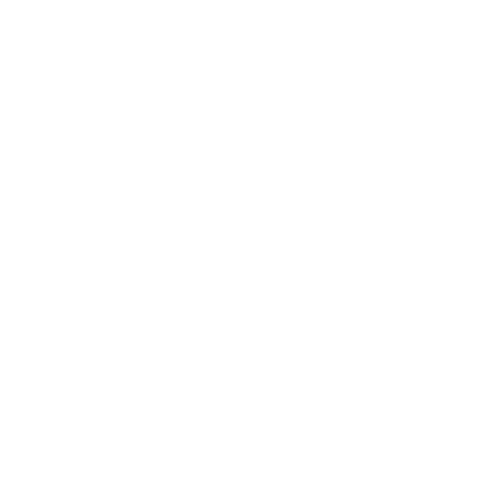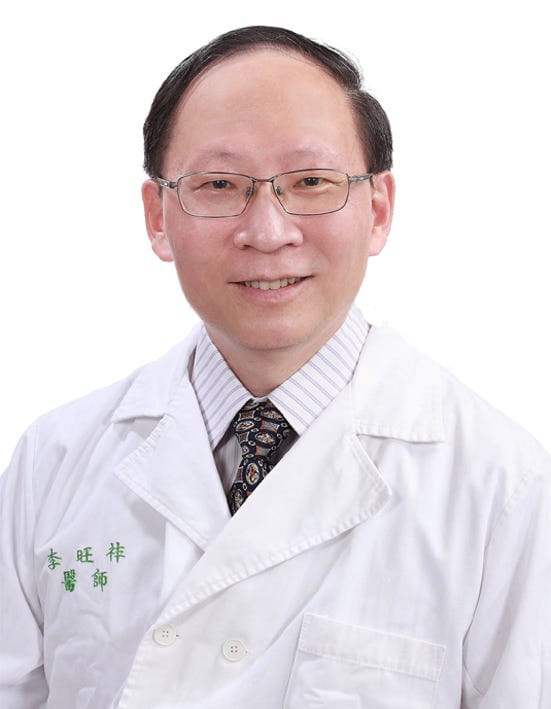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漢特博物館參訪記
原文刊載於《臺大醫訊》第十三刊(急診:等待春天)

原文刊載於《臺大醫訊》第十三刊(急診:等待春天)
撰文/med02 王紫讓
年中時分我棲旅倫敦。六月二十六日早起之後,自下榻旅館步行出發,穿過攝政公園東南角,於大波特蘭街(Great Portland Street)地鐵站上車,地底穿梭半個倫敦市,在聖殿(Temple)站重見天日,從地鐵站出口的小販順道買了一盒台灣見不到的覆盆莓,苦澀尖酸中帶著幾乎嘗不出來的微甜。空氣沁涼宜人,建築悠久雅致,我開始一天的徒步旅程。
聖殿區乃倫敦名校雲集之地,著名的四大律師學院(Inns of Court)──葛雷、林肯、中殿、內殿──皆在此處,皇家法庭就位於地鐵站出口不遠,在此漫步一不小心便會走進倫敦政經學院(LSE)的範圍。拐個彎就到了大名鼎鼎的艦隊街(Fleet Street),倫敦所有報社的大本營,集合了全英的消息情報,誠如一位英國作家所言:「在這裡,人們要變笨都很困難」;從艦隊街一條甚為隱密的小巷潛入,在中殿與內殿奇特的氛圍中穿行,左方一棟圓形建築坐鎮,是的,這就是《達文西密碼》中鬼影幢幢、萬分神祕的聖殿教堂(Temple Church),現在只要附上三鎊,誰都可以入內參觀。
以上都只是陪襯出本文的主題: 英國皇家外科學院(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漢特博物館(The Hunterian Museum)。我慕名已久,專為這所博物館而來,但卻不太好找。它藏身於倫敦政經學院的建築之中,走過幾個充斥垃圾,氣味並不太好聞的巷弄街口,與兩位正在巡邏的高大警員擦身而過,穿越林肯法學院青翠動人的中庭,才找到這棟不太顯眼的建築。

英國皇家外科學院創立於1800年,由外科醫師公會改組而成,自此,英國的外科醫師正式登記有案,成為皇家機構,受政府的法令認可,擺脫了低下的「理髮匠與開刀人」之蔑稱。造成此原因的結果大概就是數年之前,一位高深莫測的天才,永遠改變了外科醫師的執業方式,使之從純粹的機械式刀匠工作變為以科學方法為基礎之生理、病理研究,並大幅提高了外科醫師的社會觀感與地位。這位不世出的天才便是漢特(John Hunter, 1728~1793),畢生追尋真理的獵人。
這樣說或許有些抽象,不過,一想到他為牙齒命名,也就是發明了門齒、犬齒、臼齒的稱呼;第一位系統化研究發炎反應,並提出發炎其實是一種身體治癒自己的方式;在一七七六年利用針筒完成史上第一次人工受孕;精通幾乎所有動物的比較解剖學,並且成功將將外科手術與病理研究結合;同時身為博物學家、比較解剖學家、外科醫師、牙醫、獸醫,並且與其他同僚創建了倫敦獸醫學院;一生蒐集其醫學博物館的藏品,達到一萬四千件標本;鼓勵學生進行科學實驗並挑戰僵化教條,其中最有名的學生就是發明種痘疫苗的金納醫師(EdwardJenner, 1749~1823)。如此即可見漢特影響力之深鉅遠大。
總之,我走進了幾分蕭瑟陳舊的皇家外科學院中庭,老遠就看到外科學院的漢特博物館參觀海報,完全免費,不過由於標本古遠珍貴之故,博物館內全面禁止拍照。在大廳換了參訪博物館的牌子,隨即走上迴旋梯,階梯旁的牆壁懸掛歷任外科學院主席的肖像畫,漢特博物館就位於二樓階梯盡頭。

博物館整體風格相當現代,挑高的天花板、冷峻的牆壁顏色、玻璃櫥窗與聚光燈,似乎是在醫學叢林中探險。首先吸引我的展品,是入口左方的四片深色等身大木板,上面貼有神經與血管標本,構成四具人體的管路圖,僅憑目視便可知年代十分久遠,看了旁邊的說明後赫然一驚,發現這四片木板是1594年義大利解剖學家的作品,後來輾轉進入英國。館內有一群年紀與我相若的醫學院學生在此參訪、寫學習單,青春的喧鬧卻使櫥窗中的標本更為寧靜經久。
顧名思義,漢特博物館內絕大部分是漢特醫師的收藏,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藏品已永遠毀於二次大戰的轟炸之中,再也不可復得,然而博物館的幅員還是大得超乎我想像:位於外科學院二樓的博物館本身又分為兩層,每一面牆都充滿著標本瓶罐,漢特最富盛名的標本,「愛爾蘭巨人」身高七呎七吋(約277 公分)的全身骨骼就在長廊盡頭睥睨一切。
我實在無法枚舉博物館裡數以千計的藏品!人類器官、骨骼的標本都極有病理學價值,包括嚴重骨質疏鬆而脆裂的頭顱、整個纖維化的增生子宮、一條三段側彎的脊椎、無數的腫瘤標本,有些藏品令我感到恐懼,不禁回想起當年古人所受到的病痛何等巨大,以及漢特憑一己之力,居然能看過並處理如此豐富繁多的稀有病例,我想現在的資深主治醫師也做不到。當然還有顯露漢特於組織移植功力的絕妙案例──移植於雞冠上,卻持續生長的人類犬齒;此外尚有極多動物解剖標本及病理標本,數量之多,令我絕望,想要每個都詳細看過根本不可能,深為自己所學甚少而感到懊惱……
離開博物館,參觀旁邊的圖書室之後,走出皇家外科學院,此時已是正午。我到林肯法學院的庭園長椅坐下,吃著被壓扁且剩下半盒的覆盆莓,努力在大量知識衝擊之下保有一絲清明的思慮:這才是真正的醫學人文,我們台灣永遠都無法企及的高度與脈絡……所謂現代醫學的人文背景,其實就是指西方醫學的傳統與變革。我們在十九世紀末時,方有現代醫學傳入,我們的先天遠遠不夠。但後天也未見好轉,因為殖民政府刻意壓抑知識分子的培育,所以台灣日治時期上許多重大的政治社會運動都由醫師主導,這是東南亞殖民地的共通現象,然而,戰後政治環境也不容許思想自由,所以醫學系的神話至今仍在。
為什麼本系大聲疾呼醫學人文?因為我們缺乏人文底蘊,內部卻仍有教條主義、權威主義的幽靈在活動,用大量的課程與背誦僵化思考。現在的醫學人文課程,仍然是附庸風雅多過苦心孤詣。其目的更是令人起疑:試圖用幾堂敗絮其中的膚淺人文課程,試圖培養「醫德」,我認為非常不切實際。醫學人文的主體應基於徹底研究醫學史,而不是唱高調的「醫學倫理」。
漢特以醫學革新者聞名,在傲人成就下的,其實是用他難以估量的熱情,不斷對抗僵化的傳統醫學體制。他曾經想進入聖巴托洛繆醫院,但因為該醫院過於迂腐守舊,所以寧可進入較為自由的聖喬治醫院實習。如果他選擇前者,那或許永遠不會有漢特了。何其有幸,他的對抗終獲成功,使醫學進入嶄新的十九世紀,在這個時代,所有的外科醫師都可說是他的門徒。

漢特沒有墨守嚴厲的教條,而是鼓勵其學生懷疑、實驗、不輕信權威。他對於真理的永恆熱情,對於醫學的細膩求證,超卓的學術成就,以及科學精神的應用,於現在特別值得我們學習反思。我在此引用《蛇杖的傳人》中,一段評論漢特的文字作為結尾:「對約翰‧ 漢特而言,正式的學校教育是多餘的,而一般用以獲得知識的正規方法對他反而是種阻礙。我們不應將之視為我們的同類而嘗試著去找出其創造力之源。我們只要在他們仍存在這個俗世上時,能向他們學得一些什麼便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