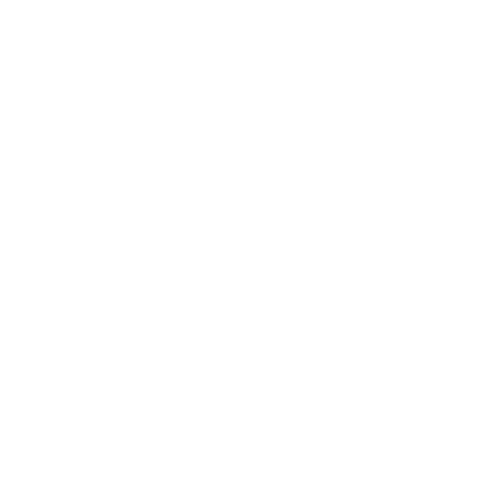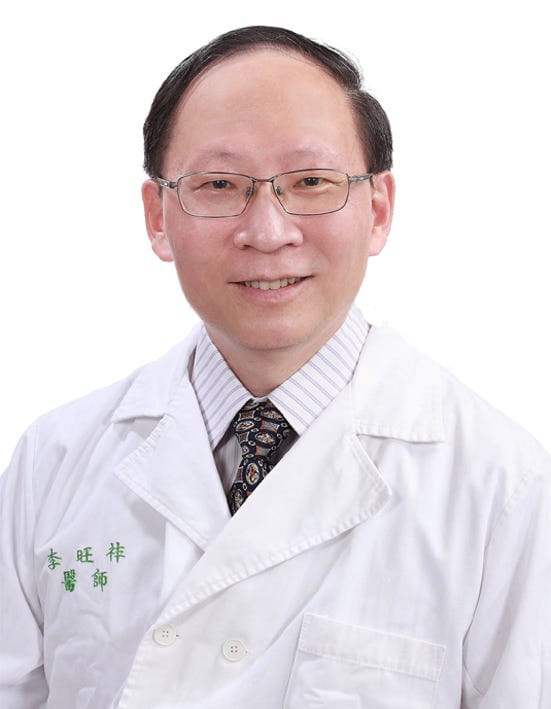白塔、左翼、《醫訊》: 追憶消逝的1950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四刊(世代)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四刊(世代)
撰稿:b99陳亮甫
楔子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國民政府接收了台灣。脫離了殖民政權,島內群眾對新的統治者懷抱著極高的期待,望其能夠紓解戰事帶來的紛亂與流離。然而新政權沒有給人民帶來希望,軍紀渙散、吏治混亂、經濟崩壞日發嚴重,一波接著一波的爭亂與省籍衝突,高壓統治下,失望透頂的人民終於對執政當局發出了怒吼。1947年,取締私菸的槍響點燃了已隱隱燃燒的怒火,大小規模的反抗在全島各處遍地開花,一直到軍隊壓境,大規模的 鎮壓與屠殺型的掃射,將這反抗勢力弭平,之後所頒布的清鄉政策以及戒嚴令,暫將政局維持在一個恐怖的平衡當中。
然而,二二八的傷痕與記憶沒有在武力鎮壓中消隱。當武裝反抗或是體制內的談判都無法撼動現行的堅實體制,學生、青年、農民、藍領勞工,開始將希望轉向另外一股赤紅的勢力。早在二二八事件以前,中共就已將矛頭鎖定台灣;隨著國共內戰亦趨白熱化,國民黨軍隊漸露敗象,中共看準了台灣將可能成為下一個敵軍的據點,早以潛心準備地下黨的組織工作,短短幾年間。地下黨的規模由二二八事件時百人不滿,擴展至三、四千名他們以合法掩護非法,單線領導擴大成員,以各種方式經營群眾工作,為的是厚植反國民政府的力量,要為中共來台解放做接應的準備。直到國民黨軍隊大規模撤退至台灣,加以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駐守台海,共軍與地下黨解放的夢想正式破滅,訓練有素的國民黨情治人員將地下組織一一破獲,成員處以死刑與徒刑,這波史稱「1950年白色恐怖」的狂潮正式告終。
這波赤色的風暴,也深入校園當中,對當時思想左傾、或甚至只是對時局感到不滿的青年學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甚至撼動了他們的一生。以當時的台灣大學來說,地下黨在既有學生組織(自治會、藝文性、政治性社團)當中,利用已然成形的人際網路,擴展群眾,目的如前文所述,是為了在解放軍來台兵荒馬亂之際,保護生產與學術研究機構,避免國民黨政府的焦土策略。社團方面,有「耕耘社」這類生產互助合作的社團,也有「雲雀壁報社」之類的政論組織,和眾人所熟知的「麥浪歌詠隊」,學生自治會方面,則在二二八事件以後,以法學院、工學院、醫學院為區分,各自成立了「學生自治會」,除了照顧同學們的日常生活需求,也是當時議論時政、推廣議題的重鎮。以醫學院學生自治會而言,幹部出版刊物、成立讀書會、播放藝文電影,擴展知識,凝聚群眾,在當時的校園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前述的白色恐怖,白塔內的學子亦難倖免於此,拾起手術刀,背誦著生理學原文的同時,他們的生命也和時帶的命運產生奇妙的交會。今天故事的主人翁,葉盛吉與顏世鴻,便擔任醫學院學生自治會第三與第四屆的常務理事(等同今日會長職位),也很弔詭地都加入地下黨的組織,負責「學生工作委員會台大醫學院支部」的工作。
催生《醫訊》的手:葉盛吉的徬徨與執著
葉盛吉生出生在台北,因年幼時母親過世,由居住於台南的叔父葉聰扶養長大。葉氏是鹽水地區的望族,在葉盛吉的父輩始沒落分家,而葉聰於新營鹽水港的製糖股份公司總社服務,葉盛吉因此能夠在富足的日式家庭中成長。
進入新營公學校、台南一中就讀,葉盛吉的求學歷程可以說是相當順遂,成績名列前茅。中學畢業之後葉盛吉旅日度過了兩年困頓的重考時光,終於在1943年進入了仙台第二高等學校就讀,並且在之後進入東京大學醫學院就讀。戰後葉盛吉申請轉學回台灣大學醫學系,繼續完成學業。
葉盛吉的求學過程曲折,而他的人生哲學與邏輯思想,據其自述,也曾經有很大的震撼與變革。作為臺人,而在日式教育中成長、接受日本體系的教育,卻又在求學時期面臨了二次世界大戰、家鄉政權重又回歸中國政府。對他個人而言,「民族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思考難題,特殊的人生際遇也讓他最終有了對於「中國」與「日本」的雙向認同歸屬。時值戰亂,學院內流行的「猶太研」(反對猶太,鑽研猶太人對民族、社會之害得學問)也一度吸引葉盛吉,雖然他最後有所感悟而揚棄之。留日學習時,葉盛吉偶爾「跟蹤」因戰亂失去家園的遊民,與他們相談並且給予生活上的資助,這一類對於社會現實的觀察,培養了他對於無產階級更深厚的理解。
返台後的葉盛吉,曾擔任台大全校學生自治會理事、台大醫學院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宿舍自治會幹事等職務,主要負責文化相關的活動, 播放電影, 歡迎市民大眾以極低廉的價格觀賞, 同時組織讀書會, 閱讀《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這類的書籍,甚且投入編纂報紙諸如《醫訊》、《東門》等刊物;至於學生福利部份,為了向當時台大莊長恭校長陳情,他還親自到機場去「追回」辭職剛要離開的莊校長,相關事務,不勝枚舉。
編按:轉述自吳寬墩醫師之補充:「葉盛吉前輩雖然於1948年有發行「醫訊」的意願,但是目前找不到當時的刊物。隨著白色恐怖的肅殺,這本刊物的命運無人知曉。1970年醫學系二年級生杜永光,有感於醫預科學生和高年級學生聯繫不易,創辦了「台大醫訊」,做為醫學生溝通橋樑。為隔週一出版。我詢問杜教授,他並不知葉盛吉曾出刊過「醫訊」。1980年代,「台大醫訊」仍每隔週一出刊。」
葉盛吉本人思想如左傾現無從得知,惟從其所閱讀書籍《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等可略窺端倪,而當時社會的不平等、政治亂象以及對於國民政府的反感,逼使當時青年的思想基進化,左傾/ 純粹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帶有嚮往,似乎也是可以理解。在醫學院學生自治會第一任常務理事劉沼光的帶領之下,葉盛吉加入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隸屬學生工作委員會醫學院支部,並且吸收顏世鴻(詳見下文)以擴大組織。求學過程中,葉盛吉相當早就發現自己對於醫學不感興趣,在畢業後選擇了公共衛生作為往後的目標,前往潮州的熱帶醫學研究所從事研究。1949年八月起,「學委會」的上級們一一被捕,並且交出了葉盛吉的名字,1950年五月,葉盛吉在屏東落網捕,當年秋天與同為「學委會案」被捕的十一人,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判處無期徒刑,後再由蔣介石改判為死刑;留下遺書給年幼的稚子葉光毅之後,他在馬場町刑場結束了僅二十七歲的青春年華。
「我自始至終並無顛覆政府的意圖。」在遺書上留下這句話的葉盛吉,是怎麼看待這些行動的呢?天生的romanticist的性格,卻同時保有醫者humanist的個性,葉盛吉或許一直在尋找著顛覆政權以外,建設良善社會的方式。那雙曾握筆編纂《醫訊》的手,在將要倒臥刑場的前一刻,料想依然是堅定,沒有半分顫抖的吧。
「士為知己者死」的人道社會主義者:顏世鴻
顏世鴻於1927年出生在高雄旗後,父母親都曾參加抗日運動,小時候舉家遷至福建,二次大戰之後回到台灣,就讀台南第二中學(今台南一中),1946年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科。
顏世鴻自稱,並不是「生就的共產主義者」,雖然在光復後不久即讀了《克魯泡多金傳》和《聯共黨史》等左翼書籍,對於其中反抗者的境遇感到同情,但亦不乏其批判與人道主義的觀點。在醫學院中,顏世鴻結識了志趣相近的同鄉學長─醫學院第三屆學生自治會會長葉盛吉,並且於之後擔任學生自治會「文化語言部」的副總幹事。對於葉盛吉,顏世鴻可以說是完全地折服於其學識與見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知己者容」的心態下,成為其終身的信徒。
然而,在入黨宣示之際,顏世鴻與時為見證者的老張(陳水木,學生工作委員,師範學院畢業,二十六歲時遭槍決)卻有了激烈的爭辯,談及華北、東北共產黨土改政策當時,顏世鴻不改批判,認為「死者不可復活」,堅持認為對地主清算式的鬥爭手法有檢討之必要,為此爭辯許久。以此足見顏世鴻雖加入左翼反抗組織,但卻有其人道主義之關懷,不會因意識形態的信仰而盲從。
顏世鴻亦是葉盛吉於台大醫學院支部內吸收的最後一名黨員,並且在其離開學校以前,將醫學院支部交由顏世鴻帶領。1950年五月十九日葉盛吉在潮州落網(先此早有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台大醫院第三外科許強、第一外科的郭琇琮、眼科主任主任胡鑫麟、皮膚科胡寶珍、耳鼻咽喉科蘇友鵬醫師等遭逮捕),顏世鴻在一片風聲鶴唳中,一方面焦急於時局情勢,二方面也想著要完成期末考試,就在猶疑中,錯失了逃亡的契機,六月二十一號清晨,顏世鴻在宿舍遭到逮捕,移送刑警總隊。經過監禁、審判,自此開始了十二年的監枷人生,在安坑軍人監獄以及火燒島消磨盡青春年華(還有在小琉球的一年半,但這是後話)。
出獄以後的顏世鴻,無法回到台大醫學院就讀,幸賴當初傅斯年校長僅以其缺考退學,學籍還保留,因此顏轉而到臺北醫學大學完成學業,後考取醫師資格,懸壺濟世度過下半生。現居於台南。
與同案的諸多學生工作委員相較,顏世鴻的倖存,宛如見證者的角色,其所留下的《霜降》、《小滿》、《初分》等傳敘性的書籍,儼然一段白色恐怖的銘刻,記下了反抗者的容顏、統治者的姿態以及動盪時代背景下的一樁樁悲喜劇,筆者本篇文章多摘要於《霜降》一書,數度翻閱,每每神色為之哀戚而儼然。
尾聲
本文可以說是日前甫於台大落幕的「【推開白色的記憶之門】─台大1950年代檔案及影像展」之遺緒,摘取其中對於時代以及校園背景的描摹,特重醫學院這一個區塊,或有期待以《醫訊》為線索,勾勒醫學生之反抗系譜的企圖。為此,雖力求尊重為文者(楊威理先生《雙鄉記》、顏世鴻先生《霜降》)原意,卻仍恐有斷章取義之嫌,還望讀者能夠見諒,以及,不因本文之描寫,曲解了對於時代背景的理解。
回想起與現任《醫訊》主編開始進行1980年代,醫學院學運史的訪談,當時的企圖是明顯而大膽的。現實生活的種種,運動、倡議上的受挫,讓我們轉而期待從歷史之中,尋找突破的契機,甚或者,只是希望藉由前人的口,講述我們對於當代社會、校園環境的嗟嘆。這樣的動機,一時不察,卻往往將訪談與書寫,引導到一個後設的自我情境,將先前反抗者的行動內涵,片段地置入已然構設的故事框架,似乎能令人看見激憤人心的前人血淚,卻也恐怕偏離歷史研究的真義。
上述與其是針對我們的訪談結果(本刊學運史的其他部份)所為之批評,倒不如說是耙疏文本、口述歷史的時刻,不斷對自己所提出的警示。涉及歷史的文章當中,我們已經盡可能地客觀地呈現、將事實予以揭露─完全沒有立場只是個虛構的幻想,但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僅是將讀者帶往被紀錄者所身處之情境(時光倒流,白塔內),而其餘的反思、評判、啟示、警醒,這部份的責任,就交由讀者自己來做決定。
※
如果允許,我希望這些問題,在閱讀完文章之後,都能夠被思考與討論。是什麼樣的原因、政治機會結構,能夠讓這樣一群身負專業與社會期待的社會精英,選擇走上一條沒有盡頭的反抗之路,在黑暗當中踽踽獨行,面對強權而能有最堅定的批判,甚而如同其罪名所述,「意圖顛覆政府,並著手實行」?
「我總覺得,團體或國家者,其中有與國家或團體相悖反的分子之存在,是極關重要的。因為這樣可以經常保持反省的氣運,而這正是進步發展的途徑。」這是葉盛吉在他自己的往日手記裡頭,記下的一句感慨。而今天的我們,對於公義的追求,對於社會現況的不滿和反省,總是存在著的,只是這樣的心態要怎麼投入形塑我們理想的公義社會,醫者的角色又該是何如?
前人以身為度,血染的風采只能作為某種嘗試性的應答,或許合理的解釋,還存在時代中,每一個書寫的、倡議的、執筆的、農作的、握著手術刀的,行動者身上,不曾有過真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