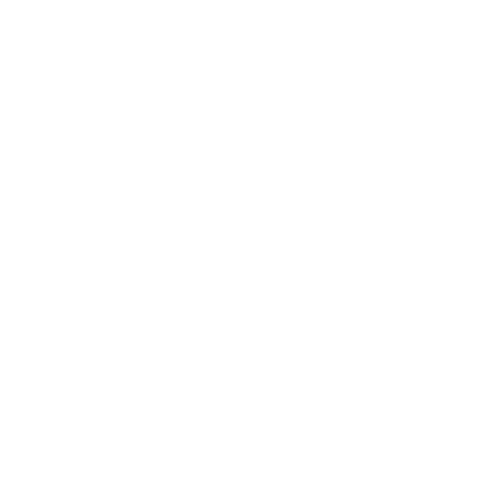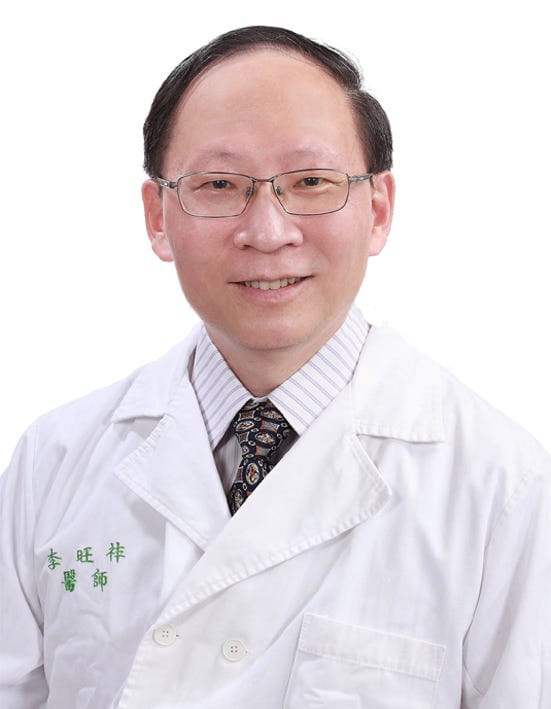疫病的管制:關於免疫共同體與治理性的考察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十九刊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十九刊
撰文:b10 廖彦宥
「你的確如此公民地無藥可醫,否則的話,你其實健康得足以為所欲為。」 — Thomas Mann《魔山》
前言:歷史的高燒
新冠疫情對於人類社會、文化、生活造成顯著的影響,疫情帶來的恐慌與心理壓力帶來一種立即的無償性,卻不帶來任何效益。許多權益的爭取在這種例外狀態下受到擱置,政府治理將人的行為化為一連串的統計學加以管控、計算風險以求完全的消除疫情。在這個境況下,各種存在於社會中的議題似乎成為次要的問題,不再得到重視。而隨著疫情逐漸淡出人們的目光,人們似乎將疫情拋諸腦後,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的懷抱,然而真是如此嗎?這次新冠疫情和政府的管制是否能帶給我們甚麼啟示?
在疫情期間,我們重新理解到醫學的決策似乎難以達成所謂的共善。從世界衛生組織的反覆言詞、疫苗與疫苗陰謀論的角力、歧視政策與反全球化的興起,都一再地告訴我們即使是被我們視為最純粹的實驗室都存在著被意識形態插手 — 或者說,實驗室本身就是當代社會意識形態的來源 — 的空間,證據本身與證據的解讀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
病毒不會依照政治學原理以及民族國家之疆界行動,病毒的流動讓許多國際政治的普世主義訴求如今看起來都難以實現,甚至讓許多社會問題與現象更加清晰。全球化在新冠肺炎的考驗下無比脆弱,做為人類對於全球化崇高理想的象徵的世衛組織的失能,使我們回到了以國家為基礎的治理範式,並以此鞏固自身民族共同體的想像力。Friedrich Nietzsche曾經在《不合時宜的沉思》第二篇中諷刺地說到:「我試圖把這個時代有權引以為傲的東西,即它的歷史文化,理解為一種弊端、無能和缺陷。因為我相信,我們都在被歷史的高燒所毀滅,而我們至少應該認識到這點。」我們得以巧合地想見,新冠肺炎在徵狀上正隱喻地成為「歷史的高燒」,向我們揭示這個技術時代的病因學。
而在疫情的政府決策中,我們也能發現醫學與政治存在十分深切的關係,或者說,疫情期間的政治主體就是醫學。政府透過徵收所有的醫療資源,以各種方式的指引去指揮所有的醫療人力;相對地,專家學者也被邀請入疾管署大樓,去擬定新一輪的防疫手段。這種中央集權式的醫學 — 政治關係並不是疫情變故所造成的偶然,而是一種治理性上的必然。即使沒有疫情,衛生政策的決定,如流感疫苗的分配、公共衛生設施的建置或健康保險相關的政策,本來也都依循著此種高度專業化的模式,只是這個狀態在疫情期間顯得十分地明顯。例如,在罕見疾病藥物的審查會議上,可以沒有罕見疾病家屬代表的實際到場發言,但絕對不能沒有專家學者帶來的實驗統計數據。
透過這些現象,使我們開始反思:醫學與政治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是如何產生的?當我們在說:「防疫視同作戰」的時候,我們為何要將疫情視為一場戰爭,使國家可以以緊急狀態為名,獲得我們自願上交的自由?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政治上的共同體是否也存在著一種生物醫學性的隱喻?透過這些問題,我們能夠更加理解疫情的管制是如何可能,以及當代的共同體想像是如何地塑造各種衛生與健康政策,管理我們的身體,或更深層地說,共同體是如何透過對於他者的建構、排除、容納,來獲得獨佔護法 — 維持秩序與抹除風險所需的 — 暴力的正當性?在瘟疫過後,我們是否能夠從燒熔而重新凝固的理性中,看到那些我們在瘟疫的高燒中被刻意忽視的,生命的危脆性?
當代共同體的建立

在理解這些問題之前,我們或許可以思考當代社會抗擊疫情的主體,也就是國家,其作為一個共同體,是如何造就這一系列的生物政治結構的?Roberto Esposito曾經指出,當代社會的政治範式免疫性的。當我們在探討一些公領域的主題時,我們常會依賴於這樣的思維模態,即自由是免於某種個體所不悅的狀態的自由,如我們可以定義言論自由是免於受到任何權力實施言論管控的自由,居住自由是免於受到移動限制的自由等。即使這常被批評為是某種「消極」的說法,這些都在某種程度上呈顯了自由的本質,即向著虛無而生的否定性,為免於某物成為權利的賦予。而正是這樣的否定性,造就了共同體的自然基礎,即人會因為免疫 — 而非Thomas Hobbes所謂「人與人的戰爭」 — 不約而同地組成一個共同體,確保自身得以免於處在不悅的狀態之中。
共同體透過免疫的否定性,形成主權去排除異己,使得共同體的狀態得以存續。而在共同體中個個體則必須去屈從於共同體強大的內在秩序,並以此獲得免疫於他者威脅的權利,這種權利是自由的存在基礎,是純粹的政治生物學運動。因此,當我們論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時,講的不是人的本質,而是自我角色怎麼成為社會生活展演中的產物。而人如果要真正實現這樣一種以「無本質」呈現的本質,就必須不斷拋棄既有的生活方式,而將自己的生存和行動投射到可以實現這一純粹「無本質」狀態的、外於共同體而不能被描述的生活狀態之中。誠如Erving Goffman所言,只有將人在共同體中進行本質化的界定,人作為概念才能被認識,能被視為本質的人因此不過是對社會結構中象徵情境連續的反應。而人的本質,也被重新呈顯為個體用以為滿足特定社會架構中的情境要求,而馴化自身的傾向。
自我因此並非穩定的內在真實,而是社會生活的不穩定成就,是一種被規訓而為自由的表現。而就是這樣的「非我之我」必然導致這樣一個命題的產生:人若想要返回其原初狀態,則必須徹底拋棄其人性,與抽象社會規範的具身化為自身存在的形式。我們如是發現了這樣的悖論:若想要讓社會對人實現真正的補償,人就必須徹底放棄 — 或者說,從來都不存在的 — 自己的原初狀態,放棄共同體對人的一切補償,融入抽象而機械的社會體制中,以自我分化的方式展開自身,並以此認識、行動。這種通過非補償進行補償的免疫機制,最終塑造了現代社會的理性運作。該系統試圖將人類自然特徵的自主性和偶然性轉化為器官和結構,以實現特定社會功能。可以說,這種免疫機制的最終目標將是徹底將自然生命轉變為理性化和機械化的社會生命。
在社會本身的理性形式中,個人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才得以永久存在。然則這種理性形式並不傾向於同化每個個體,相對地,多元而分散反而能夠維持共同體內部的張力。不同的生命形式基於不同的方式和聯繫形成一個寬鬆的聯合體,有時會以社會階級、文化表徵等形式相互排斥和對立。因此,即使共同體中的部分內部因免疫行為而被排斥,導致死亡,剩下的生命形式自然地形成新的連繫,甚至將排斥的部分重新融入共同體。在使它們無害後,它們被吸收為共同體的一部分。我們因此發現了生物與政治之間的雙重之見,利維坦在免疫範式中獲得了生物般的運作機制,做為生物的個體則獲得了群體生活的政治性。德國醫師Rudolf Virchow如是說:「醫學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科學,而政治則不過是大規模的醫學實踐。」
我們接下來得以想見,共同體不僅不會將自身的一部分排除在外,還努力擁抱外部生命形式的異質性。原因不難得出,即由於免疫政治社群本質上是由不同異質生命形式的鬆散混合組成的,更多的異質性不僅不會成為理性化基於免疫的護法暴力,而且還使社群的組成部分能夠在免疫過程中更好地適應彼此,從而增強共同體的團結。就有如身體本身對於外來器官的免疫排斥反應一般,無論這個外來者能給予我們甚麼好處都不甚重要 — 這不是大腦應該決斷的事情 — 對於外來者所帶來的「風險」,免疫系統被授予甚高的權限,發炎不適在所不惜,這些都是「必要之惡」。套用Peter Sloterdijk關於泡沫和氣泡之間關係的洞察來描述共同體和個人之間的關係:氣泡是獨立的但相互依存的,氣泡間彼此共享著氣泡壁,而許多氣泡造成的空隙卻成為歡迎外部異質性的空間,但此空間卻又需要共同體將其內部化才能證實其做為他者的存在。我們可以說,個體變成了免疫政治範式下的結果,而共同體則悖論地成為其原因,代表社群內所有個體的意識,充當保護免於外來侵害的生命的主權。
從此,我們可以利用一連串的隱喻來去形容一場瘟疫:細胞構築了稱為人體的共同體,他們彼此獨立又彼此需要,以確保人體的存續,避免自身單獨地受到他者的侵害。病原體則被視為他者,而身上可憐的細胞便成為免疫系統需要保護的對象。病原體在體內殖民細胞為其繁衍以壯大勢力,而免疫系統就有如警察或軍隊,巡邏監視細胞是否安守本分,有無謀通匪諜。細胞自身則要遵紀手法,正常地發揮其在社會上的功能,避免被誤認成癌細胞而被取締。而平行地,我們對於外來者,如國際移工的規章制度也顯示出了免疫的特質,因為他們不同於我們,我們需要對自身進行免疫抑制,或是對其加上標籤,或是將其牽制甚至毀滅。而對內的少數群體,如文化弱勢者、精神疾病者,我們則是將其視作癌細胞,治療上要避免其擴散,或者將治療 — 同化以能夠吸收為共同體的一份子,使其得以正常進行社會所賦予的工作。而這些外來者的建構也自證了免疫系統的優越性,在政治演化上也更加地給予免疫系統更多權力,以應對更多風險。
醫學與政治的哥蒂安之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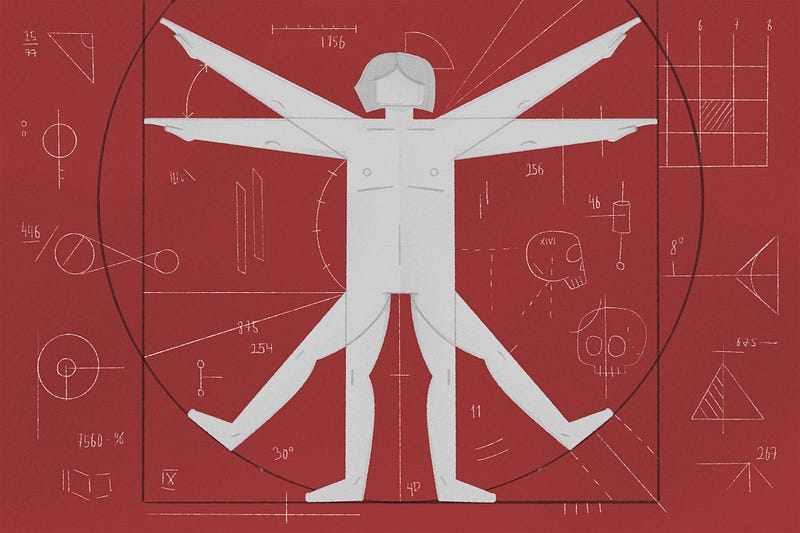
透過對於政治與生物之間的免疫性模態,我們得以發現如諸事實:誠然,生命天生就有免於不悅狀態的本能,但是共同體之主權必須被視為後設的免疫部署(Dispositif),源於生命,卻又抹除生命對其的作用,造成了在生命之上的超越性,凌駕於生命的壓迫使得生命達到瀕臨毀滅的程度。表面上,人們在接種疫苗後,自然地獲得了免疫力,而這一自然背後,仍然是國家權力依賴技術、實驗和計算所進行的干預和決斷。我們自發性地獲得了免疫能力。然而,免疫知識的反思建構並非來自於自然,而是來自於權力。
當Louis Pasteur與Robert Koch發現細菌或病毒可以做為疾病的特定原因時,是純粹的科學上的意見(doxa)。然而如果要讓其成為共同體的信仰,則需要共同體內部所有個體透過各種透鏡 — 包括攝影機、水晶體 — 的見證才得以實現。而這種見證的結果促成了名為「病原體」的信仰,打破了從希波克拉底以來的體質醫學派典(paradigm),科學方法對於分類醫學的侵入產生了莫大的不確定性,使得醫師必須放棄各種既成不變的理論與文化秩序,逼迫自身重新面對病患的實際情況。醫學本身因此變成了司法:如同法律的建立、修正與執行,實驗室與醫局的醫師們透過集體的審議或修正,形成如法律般臨床指引,並以此處置當下的病人。而另一方面,也正因為疾病做為他者的輪廓 — 從模糊不清的體質轉變為單一個來源,Kojin Karatani將其稱之為「神學式」的對立(註1) — 而變得逐漸清晰,使得風險成為可以透過統計而得以量化,而主權因此可以做出更加基於「自然」且符合工具理性的部署以控制人民。
我們可以如此說,早期的 — 或者以Zygmunt Bauman的說法而言則是固態的 — 現代性在生命與主權之間保留了某種割裂二者之法律、社會或文化秩序之存在,那麼隨著政府針對人口健康、並透過民族主義追求的科技發展而始於十八世紀末出現的流動現代性,則消除了這些秩序做為可靠的參照系。原先不可見的風險在流動性中成為唯一的變量,生命因此變成直接的政治對象:主權進行以醫學等科學為基礎的現代性治理,且這樣的治理性(govermetality)是對生命本身的治理。因此,在針筒與統計報表之外,再也沒有任何令人嚮往的神奇可觀之處,阻擋我們在免於風險的路途上前行。而現代醫學也正立足於此,風險構成了生命政治的依據,而主權則被賦予管理、監控人民健康的權力,對於風險的恐懼與焦慮支撐整個免疫共同體的穩定。主權為了排除風險,醫療系統必須竭盡所能地蒐集所有的人口地理資訊,將其範圍毛細管般地伸至每個個體,並集合起來進行風險計算,以經濟生產力為核心,建構出健康的標準。
醫學與政治的結盟,也造就了現代醫療體系的基本樣貌:中央集權與官僚政治。Michel Foucault提出了「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概念以表現出當代醫學與政治相關性:一方面,醫學需要政治的背書,使得醫學實驗者能夠透過以為了人類崇高的「知識」追求為由,進行各項對於人體的實驗性嘗試,以獲得更多的知識,鞏固自身在社會中的所扮演的權威角色。另一方面,政治仰賴醫學獲得其控制人民的自然而正當的權力,透過各種統計學與生理實驗數據所獲致的知識,政府得以以人有免於各種風險的自由作為自己的「權力」的依據,向人民的身體達成知識的部署。我們因此得以理解這樣的知識 — 權力結構:醫學知識的產出,有賴於政治部門的首肯,政治權力的賦予,則指望醫學實驗的數據。醫師們因此不再相信諸如四膽汁、陰陽調和等將自身的文化秩序前設於觀察的學說,相對地,醫師將詮釋權讓位予病患的軀體,醫師僅僅做為一個觀看者而存在。疾病不再是外於軀體,如百科全書般分類學式的狀態,而是實證的、無法脫離軀體而被談論的現象;死亡也不再是醫學的終結,而是醫學的起點,一切的醫學知識都藉由人的死亡而鮮明起來。死亡的觀看因此在臨床醫學中與生命和疾病形成三位一體,成為知識 — 權力的產出來源。
然而,這一切都還不夠,為了制定人民的健康標準並進一步深入,這些生物生產與維繫生命的生命政治治理手段開始將個體責任化,使其積極的參與自身生命的控制,即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下的自我治理。而在疫情期間,主權也試圖將傳染進行道德性建構,所有人都必須為了不被傳染而竭盡心力,而若是成為染疫者,則共同體中的各種透鏡將會將個體集中在屈辱的目光下,使得個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責,彷彿自身的生命被流放於共同體之外,成為純粹的、生物性的狀態。而這些個體受到醫療系統的嚴密監控之於,又諷刺地成為不可多得的醫學研究素材,為崇高的人類智慧盡一份心力。Giorgio Agamben所揭示的「裸命/牲人(la vita nuda/homo sacer)」正迎合著如斯狀態:既背負著所有人的目光之餘,卻又帶有某種不可侵犯的神聖性。在大疫年之下,鄰人不復存在,所有人都變成了所有人的他者,抗拒著、或已經成為了裸命。每個個體彷彿成為了共同體中悄然無息的螺絲釘,在恐懼與焦慮的行為反射下,為抗擊疫情而服務。現代醫學因此已從單純的治療技術與知識,轉變成對於維持健康的社會的治理性,監控、規範個體的生存樣態。醫療系統如同軍隊的指揮官一般,透過其在統計學知識所塑造的權力,指揮所有個體為了健康而戰。共同體因此發起了一場面對病原體的、無主語的戰爭。這場戰爭關係到生命權利、生命政治的發展,也是治理性的運作,是例外狀態的試圖常態化。
倦怠與危脆生命

而隨著資訊平台的興起,生命政治在當代得到了更加扭曲的進展。在當代社會中,所有的否定性、他者都被各種媒體形式再現、重製,使其尖銳而值得討論之處變得平滑,融入當代景觀社會的一部份。關乎自身的治理性如此之多,但對於日常生活卻又看起來如此遙遠而無意義,我或許能在平台上給予那些遊行者一些表情符號,但其重要度甚至不及在社群媒體上傳今日的晚餐:人對於自由的追求變成了自我滿足。在一個當代形式的共同體內,能做為行動主體的「我們」也已經不復存在,所有人在螢幕與螢幕的鏡像中不斷地生產、再製與鈍化,形成一個個平滑的球體,代表著避免刺傷他人,也不希望他人刺傷自身的肯定性,並就此生活在了只有自身與自身願意聽見的訊息的同溫層中:共同體內的他者成為了同者。
我們甚至能說,在新冠肺炎還沒到來之前,我們就已經遭受到其後遺症所帶來的危機:景觀社會(société du spectacle)中感官的異化,與新冠肺炎所帶來的嗅覺與味覺喪失形成了諷刺的同構性。因此,相對於過去的疫情中,病原體所代表的他者的恐懼與否定性,對於浸淫在媒體平台內的人們而言,似乎不再如此可怖,甚至令人感到 — 並非Slavoj Žižek所謂「武漢夢」(註2),期待人能對於當代社會的病因加以重視並加以重構,而是Byung-Chul Han所觀察到的,肯定性過剩的 — 欣喜。我們如何為此感到欣喜?因為在恐懼被稱讚所取代的當代,我們似乎都自認為是「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再也沒有更多的歷史教訓值得我們分析,一切的危機在制度下似乎都不值得憂懼:因為我們過去的祖先們都經歷過,也存活了下來。我們可以說,制度拜物教無疑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表徵,那麼新冠疫情的到來無疑就是為這潛在的宗教式狂熱釋放出來。疫情的管控因此是一場讚揚治理性的祭典,口罩和快篩試劑即是這場祭典的法器。
而在這場祭典之中,個體陷入了狂歡:人們積極地更新數據,瘋狂地轉貼社群媒體有關的資訊,為了螢幕上的數字感到歡欣鼓舞。政治人物透過各種醫療數據與超前「部署」的宣傳手法 — 是的,治理性不再只是空間性的,其時間性的意涵也正在被展開 — 讓鎂光燈的焦點集結在自身身上,而非那白色巨塔裡的幽暗角落:每個得到新冠肺炎而又痊癒的政府領導人無不為此獲取了龐大的政治聲量,成為媒體敘事下的成功擊敗瘟疫的英雄人物。人們近乎瘋狂地趕工各種醫療物資,口罩與酒精在家家戶戶囤積如山,做為自我治理的耀眼功績,彷彿這場戰爭就是人們存在的目的一般。而內部的制度拜物教狂熱也延伸到了共同體的外部,形成了基於制度信仰的宗教戰爭:東方長期的家長制傳統與西方的自由權利的矛盾在這次疫情中明顯地激化,開放或管制不只成為科學問題,更成為基於治理性的爭論。George Orwell式的語言恰巧完美地貼合了這種境況:「歷史在此時就像是一張白紙,被不斷的擦乾淨寫上新的內容。」(註3)這種過度生產、過量資訊使得人們產生了無以復加的疲憊感,一種基於肯定性的暴力,使得人們的心靈逐漸空虛,陷入異化的疏離感。在空虛的目光中,瘟疫做為他者扭曲變形,溶入當代社會的同質性暴力中,成為祭典的原因與結果。至此,我們可以諷刺地說,在疫情中使現代人感到寂寞的,不單單是來自強制隔離政策,更源於在愈發疏離的景觀社會下,自發性的功績主義倦怠之中。
讓我們將視角回到台灣,正如黃金麟向我們揭示的一般(註4),台灣人的身體在長期的徵兵制傳統下已經具有武裝化自身的動員預備。因此,台灣人對於這次的瘟疫所展現出采成績或許並不只是如政府所宣傳的一般,是民主自由的制度使我們願意響應政府的決策,也應該考慮過去戒嚴導致的軍事化遺存所造成的影響。在這次的疫情經驗也表明,東亞社會的家長式文化,使得政府可以在接近無阻力的情況下執行更多的治理。然而,政府的宣傳仍然有其現實之處:台灣社會在受到國際社群的長期忽視下,形成渴求凝視的仰望狀態,從過去的抗煞經驗獲得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的經驗,到現在的Taiwan can help,無一不展現出台灣正在進行一場 — 根據蔡友月的看法(註5) — 生物民族主義之戰,透過在防疫上的優越表現鞏固自身的共同體,以應對隨之而來的地緣政治挑戰。
而如今,盛宴初歇,當我們回首這場盛宴時,會發現到有許多應該被看見而選擇被視而不見的事物逐漸呈顯在我們眼前。他們是在需要定期回診領藥的慢性病及愛滋病患者、是仰賴營養午餐與實體學校教育的低收入戶、是正受到罕見疾病所苦的病患及其家屬、是長期受到汙名與偏見的國際移工、是冒著風險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送員、是為了這些弱勢族群發聲的社會學者,這些人的訴求在免疫政治敘事下不值一提,他們生命的危脆性在生物民族主義的認同中成為「不識趣」的一部分:他們既無法為了台灣在建構受到長期國際忽視下,得來不易的國際宣傳窗口期而做出貢獻,甚至還要為此付出更多的醫藥衛生或宣傳支出來照應這些在疫情下更為脆弱的人群,增加「不必要」的風險:在積極而倦怠的社會中,他們必須沉默也理應沉默。
在免疫政治的範式下,這群人是在內部化的他者,是矛盾與歧視的來源,他們不能被凝視著我們的西方社會所看到,也必須在特定情況下受到更多檢視。當這些被忽視的危脆生命一旦稍有不慎,則媒體便可以立刻貼上「防疫破口」等標籤,進一步強化政府在防疫政策上的合理性。但我們所忽視的是,並不是所有學童都能擁有一個不受他人干擾,且具有完善的網路設備的環境;也不是所有國際移工都能免於勞動仲介的種種剝削,並且在不受歧視的狀態下有足夠多的生存空間;更不是所有慢性病或愛滋病患者,都能在日益森嚴的疾病管制下領取他們所必需的藥物。我們終於看見了危脆性的差異:在疫情之下,並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遭受到疫情危機的壓力,在社會階層中的不同個體都面臨著各自的問題,而疫情將這些問題誠實地彰顯出來,但在共同體的透鏡與透鏡之間,這些事情卻變得無關緊要。
解蔽與自我治理

透過分析當代社會透過疫情所揭露的病因學,我們似乎能發現到「遮蔽」似乎成為這個時代的病根:共同體的免疫範式遮蔽了人的原初狀態、生命政治的建構遮蔽了主權與個體間的社會文化秩序、積極的倦怠社會遮蔽了那些不能被訴說的危脆生命。我們因此發現了一種矛盾,即當代技術的進步理應是解蔽的過程,使一切不可化約之物變得得以轉化為可以理解的知識,但解蔽過程中卻又同時帶來了更多的遮蔽。
在各種對於技術的反思中,Martin Heidegger對於解蔽(Entbergen)與技術的探問,或許值得我們回顧:用過去的角度分析,技術的本質是引致不可見者,使其得以進入表象為我所見:透過技術,人得以將原先不在場的事物,如車輪、溝渠,通過「創造」得以在場,從想像中解蔽出來,成為真實的存在物。然而,當今的技術雖然也講求如此的解蔽方式,但卻是依據工具理性為原則,科學地透過資源的釋放,並細化各種安排、儲存、分配、調節等的環節強行索求(Herausfordern)之而使其實現,這種方式被稱之為「集置(Ge-stell)」,而這種敘述則與生命政治的意旨不謀而合,即治理性的部署本身就是一種集置。
因此,自然從此不再視為他者,而被人作為資源而被集置。更甚者,人也被捲入集置之中,作為人力資源的儲備,隨時被聽候技術的差遣。可以這麼說,當我們選擇集置作為解蔽的方式時,我們也因此被納入解蔽的過程之中,從而失去了選擇其他解蔽方式的權利。而這意味著人不但只能單向度地認識環境,且對自身存有也只能以單向度進行理解,因而使得人無法認識自身。我們因此認識到,集置本身作為解蔽的方式竟然反過來成為遮蔽的來源。可見的從此變得不可見,而可見卻從此變得不可見。而從人對自然的角度觀察,我們很難再說科技是為人而存在的活動,而更可能是Bruno Latour口中的自然與社會的「混種物(hybrid)」(註6),而在現代性對於自然與社會的純化之下,科技卻仍然被遮蔽為某種可以被純粹地區分為自然或社會的產物。而這二重的遮蔽,即人對自然與對人本身的遮蔽,或許使我們對於當前社會的解方找到了些許線索。
當我們嘗試將人對於其自身的遮蔽去除時,我們得以發現自身或許仍然有其他可能:當我們受到共同體的治理而被迫居家隔離時,我們或許應該不要再將視角注向共同體內,試圖加入治理性的狂歡之中,不斷地將自身責任化、功績化,融入新自由主義的自我治理內:不再過份關心疫情的各種動態,也不再為了自己無法囤積過多物資而感到焦慮。相對地,我們應該嘗試將自身抽離,隔離這些群體的隔離生活方式,去進行過去所未曾進行的「創造」:我們回歸了與共同體共在的本質,但除了「集置」之外,我們仍然可以開展與之不同的自我治理,如Catherine Malabou所言,一種「遠距的社會性」(註7)。如果我們總是強調連結而非距離,認為這樣的直接才能拯救根植於倦怠社會中的冷漠與自私,我們將會諷刺地得到與之相反的後果:當個體忘記如何保持心理距離時,也會忘了如何無利害地審視自我與共同體之間的關係,故也無法透過對於關係的體悟詮釋自身的欲望來源。而唯有當我們懂得保持心理距離,我們則能用類似於審美的方式來處理共同體內的狂歡:試著以同理與無利害的態度,去觀察狂歡背後的各種聲音,而非以功利的角度思考與自身的關係。
例如,在瘟疫期間進行書寫或藝術創作,將在瘟疫時期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使得我們得以認識到瘟疫的不同思考角度,使人得以震懾於除了集置之外的其他解蔽可能,並且在瘟疫後透過對於例外狀態時間的見證,使人得以反思在瘟疫中的各種政治生物問題。在書寫與創造的過程中,這些行動所完成的,所見證的種種事件都將會被共同體中的個體所記憶,而這便是Hannah Arendt所稱許的,政治歷史上的不朽。又或者,我們能選擇在疫情期間更加地愛護在周圍的鄰人,正視他人生命的危脆性,直視自身的不安。對個體而言,瘟疫的傳播在喚起生命存續的行動的同時,卻不捎來任何的啟示、道德隱喻與賦予。生命對於病態與正常的二元對立中做出了恐懼的反映,即使一切都尚未發生在它身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展演因此中斷,使得社會建構不能再呈顯為自我得以依附的平台。死亡變得不再疏遠,本體的焦慮使得自我從日常生活的角色中剝離,迫使個體無助地等待那無法被化約理解的、向來屬己的死亡的來臨。這種認知,便是我們能夠重新建構與他人關係的機會,誠如Judith Butler所言,因為這「讓我們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係紐帶,此一紐帶有助於我們理解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相互依存狀態與倫理責任。」(註8)透過對於集置本身的解蔽,我們或許終於能從生命政治的治理性中脫離,並阻止例外狀態的常態化。
而當我們重新去思考自我與自然的遮蔽時,我們則會發現關於生命政治,我們仍然有其他可能:康豹透過對於台灣的王爺信仰中發現到(註9),宗教儀式對於瘟疫後的各種社會文化情緒的安撫有著十分正向的作用。Victor Turner指出,在前現代狀況,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受難儀式在瘟疫後上演,透過建造社會中所有個體得以見證的場合,即社會劇場中,人們透過各種象徵性的舞蹈、懺悔,祈求某種形而上的力量祈求原諒。這種原諒是十分特殊的,因為其客體並不是指一個特定的罪行,而常常是因為天災所造成的各種社會文化問題,如瘟疫造成的。而相對地,其主體則是某種冥冥之中的力量,可以是自然或者是神祇等一切被敬畏之構造。而在此狀態下,公共圈(Öffentlichkeit)從支離破碎的後現代狀況,透過社會劇場的再現,人終於意識到人與自然或社會的連結,使我們得以重新挖掘出被遮蔽的各種社會文化秩序中的,無法被理性所掌握的異質性,並嘗試從其中找出治癒性的力量,撫平在生命政治中所無法平復的,疫情的傷痕。而當我們發現了在疫情期間,人類的例外狀態使得自然得到了喘息,我們也因此得以重新評估自然作為他者而非可調用的資源。
代結語:戲劇的隱喻

Antonin Artaud曾經對於瘟疫與戲劇的相似性,並進行了如諸分析(註10):瘟疫與戲劇,對人而言似乎都是有益的。因為瘟疫將使得許多道德性的隱喻因此破產,並迫使人們面對真實的自我,正如在舞台上所展演的那些悲劇一般。瘟疫更使得那些虛偽與欺騙袒露在公眾的視野之下,並試圖將人從逐漸鈍化的感官中拯救出來,使共同體得以看見自身的病因,從而使得共同體得以看見改變的可能,將自身從「歷史的高燒」中拯救出來。如果說,這次的新冠疫情為現代社會帶來了一場危機,那麼等待著後疫情時代的,就不應該是一種回復,而應該是一種痊癒。因為在瘟疫之後的,從來不應該是乘載著過去病因,並隨時可能再度復發的社會,而應該是乘載著嶄新的可能性,並且能總結出自身病因的共同體。透過對於疫病管制的考察,或許我們終於得以脫離「歷史的終結」,並在逐漸冷卻的高燒中望見自身的樣態。
註釋
- 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新知三聯書店,2001
- Slavoj Žižek,My Dream in Wuhan,2021,https://www.welt.de/kultur/article205630967/Slavoj-Zizek-My-Dream-of-Wuhan.html
- George Orwell,1984
- 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聯經出版社,2009
- 蔡友月,想像的病毒共同體:全球vs.台灣生物民族主義之戰,2020,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covid-19-imagined-communities
- Bruno Latour,《我們從未現代過》,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群學出版社,2012
- Catherine Malabou,To Quarantine from Quarantine: Rousseau, Robinson Crusoe, and “I,”,2020,https://catherinemalabou.wordpress.com/2020/04/08/to-quarantine-from-quarantine-rousseau-robinson-crusoe-and-i/
- Judith Butler,《危脆生命》,申昀晏譯,手民出版社,2023。
- 康豹,2021,〈瘟疫、罪惡與受難儀式:臺灣送瘟習俗面面觀〉,康豹、陳熙遠編,《研下知疫:COVID-19的人文社會省思》,台北:中央硏究院。
- Antonin Artaud,The Theater and Its Double,pp.25–31,Groove Press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