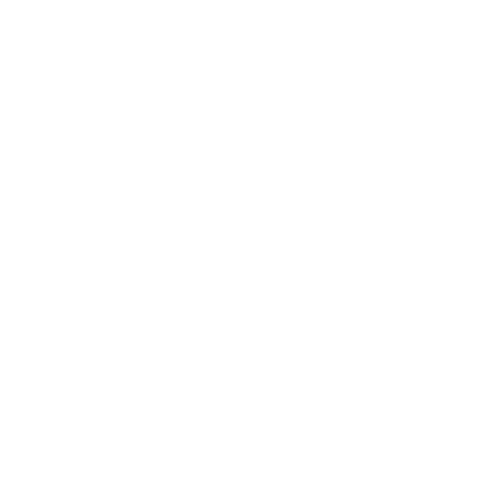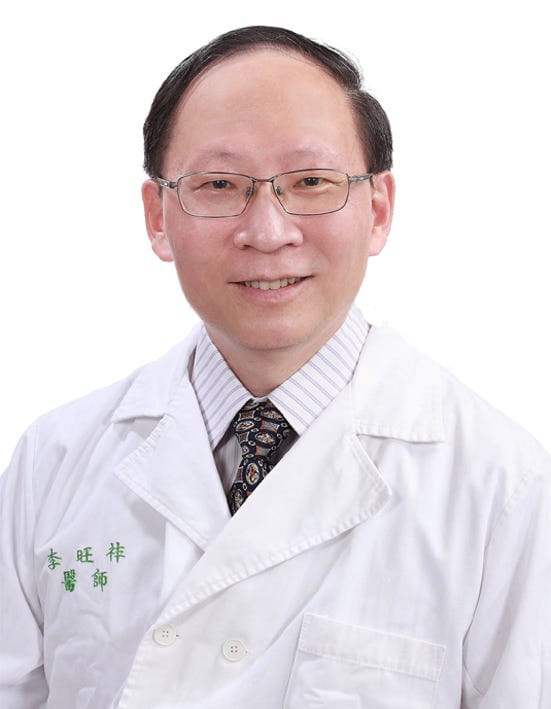再生與重建:論《精神衛生法》的修法和台灣社區精神醫療之路
原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十八刊(重生)

原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十八刊(重生)
受訪:吳建昌教授
採訪記錄:系學會文刊部 B10 廖彦宥,B07 蘇映甄
《精神衛生法》於西元1990年公布施行至今,期間歷經四次修正,卻已逾十五年未大修,近年來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認知改變,以及數次重大社會案件之影響,修法更有其必要性。歷經2022年五月初審,多次立院黨團協商,終於在2022年11月29日三讀通過修訂條文,經總統公布後,除第五章、第81條第3、4款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外,將於2年後實施。而這次修法的重點與牽涉的議題為何呢?這次醫訊第十八刊《重生》,我們十分榮幸邀請到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所)副教授、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司法精神醫學中心主任吳建昌老師,與我們分享《精神衛生法》本次修法的願景,以及實行上所要面對的現況與挑戰。
有關社區支持:
問:臺灣現今是否具備充足的社區支持能力,以容納國內之精神障礙患者?
答:誠實地說,我們尚未具備充足的社區支持能力。首先,以修法內涵論之,這次的修法主要為呼應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下簡稱CRPD)與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CRC)之精神,若以人權觀點切入,修法應提倡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支持,支持他們作成決定,而不是替代他作出決定;但臨床實務上,若以精神醫學觀點,因為醫療化的精神疾病治療方針強調保護精神疾病病人,某種程度上有剝奪其作成決定的能力的風險(例如,受到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等強制措施)。因此,以兩方理想觀點來看,修法都有尚難企及之處,只能平衡之。
修法之後的實踐,在實務上,社區支持系統需要政府不同部會之支持,例如與醫療、社會福利直接相關的衛福部、提供緊急救助的內政部、制定身心障礙者教育方案的教育部等,各部會之間的水平整合,中央與地方部門的垂直整合,以及在地執行的各單位團體之間的網絡整合,才能建構完整的支持系統。但作為一個母法,《精神衛生法》僅提供大方向的重點條列或提示,引導資源投入,後續落實更需要這次修法的27個子法規與行政規則的制定(包含修正在內),且需納入立法院27個附帶決議,可以彈性地充實母法的內涵,不需要凡事經過立法院的冗長議事程序,讓行政機關可動態地衡量如何執行,達到法律政策的目標。
問:社區支持系統現行上遇到的困境與可能的解決方向?
答:社區支持系統現今面臨到的困境,包含專業人力的培養,以及專業人士之間也會競爭有限的資源;從科學論點上來看,社區支持的相關措施可能研究較為不足,評估指標多為滿意度與疾病症狀的改善,少有將社區支持措施的主要目的(例如自主與平等)量化,因此尚缺乏足夠的科學實證來支持全面採用的政策規劃,相較於其他既有的社區支持措施,對於新的方案要投注多少資源,衡量上也較為困難。
此外,醫療端與政府端的投入,與社區支持的關係與平衡也備受討論:以醫療端介入來說,精神醫療過往或被認為與社區支持的立場相互牴觸,但實則卻可能以夥伴的角色,成為社區支持的一環,例如許多精神醫療機構皆有提供走入社區的居家訪視與醫療服務;在地方,則政府端過往經常有實際運行上的困境,例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在各地方政府的發展程度不一,有些淪為辦公室招牌,因人員多是兼任,並沒有實質運作,而即使有逐步發展,不足的地方仍需仰賴精神醫療機構和NGO去執行。在社會安全網2.0計畫中,衛生福利部將持續推動在臺灣廣設71個具有實質效能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將可以改變現今各種資源不足的窘境。
於法律制度層面上,在修法前,精神衛生法著重在在強制治療與自由限制措施的相關規範,缺乏社區支持的相關規定,因此行政機關可能較無依據以著力,修法增訂後,期許地方政府能依循母法的大方向和子法規的細項,去具體實行。
回歸到病人與家屬本身,要如何處理病人本身和家屬在治療過程中所遭受的壓力與各種問題,也是社區支持不可迴避的問題,有措施或無措施皆有可能造成傷害,而若出現以社區支持之名造成的傷害,誰要負責任?也是我們在制定與執行相關法律政策需要去思考的。
問:精神照護機構之設立造成的鄰避效應應當如何解決?
答:其實這個十分的困難,其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即為對精神疾病的迷思與汙名化仍存在著,經觀察可能仍需要好幾個世代的時間去調整觀感,透過社會整體的各種努力(包括:教育、媒體報導或文化活動等)來提升人們精神健康素養,才能有效消弭或減輕此現象。《精神衛生法》在本次修法前,只有規範各類傳播媒體之報導 ,不得使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視性稱呼或描述,以及誤導閱聽人認知,修法後除了擴大規範範圍至社團法人、團體及任何人等,也考量到病人或疑似精神疾病之人涉及法律事件時,媒體常先入為主地將事件原因歸咎於病人的精神疾病,但曾有研究指出精神疾病患者犯罪,其實大多都與其症狀無關,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大眾媒體如此書寫,將會嚴重汙名化精神疾病,因而增加規範:若未經過法院裁判釐清案件責任及原因前,不能指涉當事人之疾病是造成該法律事件之原因。
然而對於破解迷思,除了政府主導的法律規範和政策宣導、還有甚麼方式呢?法治教育如國民法官制度的實行,參與判決的民眾能更以多面向的角度思考社會事件和相關判決,而像《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類的影視作品就提供大眾很好的切入角度,用這種非教條式的方式來去迷思化,使得我們得以理解彼此,更可以減少人們排斥精神疾病患者的傾向,甚至提升人們支持精神疾病患者融入社會的態度。
問:社區危機處理機制在臺實行的困難與可能的遞進方式?
答:團隊的建構與責任的歸屬是我國在實施社區管理機制中需要解決的問題。當精神病患在社區中發生自傷或傷人的突發狀況時,最理想狀況下,需要有警察、醫師、社工師等組成的行動團隊進行有效且即時的處置。然而在我國,執行主體與責任歸屬上仍然缺乏共識。舉例而言,危機處理機動團隊最理想的狀態,莫過於在醫院中的心肺復甦緊急救護團隊,專業醫護人員、保全人員平時各自工作,一旦收到緊急呼救,馬上可以就近移動到病患所在,透過通力協作與有效的溝通領導機制,使得醫院中緊急狀況能夠被迅速完善的處理。然而,在廣大的社區,這樣的機制便容易面臨專業人員不足,機動性偏低等狀況。從實務操作而言,警察與消防人員理應站在第一線做為領導者,並在醫療專業人員趕到之前或無法趕到的情況下進行有效的處理。然而我國警消因為缺乏相關的訓練,且擔心在其處置後會被當事人提告妨礙自由等風險,使得他們對於擔任主導角色有所遲疑;雖然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9條規定警察可以對疑似精神疾病者危險行為的即時強制有所規範,警察機關仍希望在精神衛生法中明訂精神衛生人員的主導地位,此種態度可能導致一種互踢皮球的低效率狀況。
為了改善這樣的狀況,在本次精神衛生法立法修正過程中,立委提出的附帶決議有提出為增進警消等人員在危機處理過程中的即時性與安全性,要求內政部應比照基於美國的曼菲斯模式(Memphis model)中危機處理團隊(Crisis Intervention Teams, CIT)的方法,進行時數40小時的完整教育訓練計畫,補足在執行上會需要的精神病學知識,以提升警消在面對社區危機的反應,並降低執勤風險,進而可以在精神衛生人員的諮詢支持之下,快速有效地完成社會安全的維持及潛在精神疾病患者的保護工作。而在少數判斷困難的情境下,也保留精神衛生人員來擔當評估判斷工作的空間。
在後續改善上,我認為還有一些面向可以參考:在法律上,為了提升警消人員的意願,應該在法律追訴機制能有良好的保障,避免訟累。而在執行上,也應該參照人權團體所提出的社區支持方案,透過同儕團體(精神病友的現身說法、直接提供支持)和宗教場所(宗教層面的慰藉)的幫助,構建出溫暖堅韌的社區支持體系,降低患者對於社區精神醫療與支持方案的「抵抗心態」,這樣一來也不一定需要強制就醫。藉由各種方案的多元選擇,使得處理方式能夠更加多元彈性,畢竟從來沒有一種方案可以一體適用於所有精神疾病患者,所以這些方案都值得我們去發展,並且評估其效用。台灣在推行危機處理機制仍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們只能主動地從做中學習,藉由過去的案例中汲取經驗,才能構建出更好的在地化應對模型。
有關強制住院的法院審理:
問:本次修法將強制住院之裁定權轉由法官裁定,這是否會在程序處理上導致強制住院天數增加,造成人權隱憂?
答:當精神疾病病人精神症狀惡化,做出自傷或傷人的行為而被緊急安置時,目前審查會若是無法在五日內決定患者是否需要強制住院,就需要停止緊急安置,依其意願決定後續處理方針(包括直接離開緊急安置處所)。而為了實踐CRPD之精神,本次修法將強制住院改採法官保留原則,緊急安置程序仍由精神科專科醫師啟動,在指定專科醫院執行,而是否強制住院的決定權則轉由法院定奪,因法院審理需要時間,也期待若病人之症狀能在緊急安置期間改善,則可隨時撤回強制住院聲請,故原本草案希望將緊急安置期間定為十四日(目前為五日)。然而,由於緊急安置會影響到病人的人身自由,的確是有些人權團體會認為在程序上有疑慮的地方。因此在立法院協商期間,在各方的意見權衡下,最後將緊急安置期間定為七日。
即使如此,不管是七日或十四日,都無法確保法院能夠在緊急安置期限屆至前作出強制住院與否的裁定,因為依據司法院之法理解釋,法院審理時間超過緊急安置期限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繼續緊急安置仍符合程序規定。在法院裁定強制住院時,得將超過緊急安置的日數算入強制住院之日數;若法院最終裁定不需強制住院,僅發生終止緊急安置之效果。相對的,法律為了保障這些人在緊急安置中的法律權利,也向病人提供司法協助,保障其在緊急安置過程之權益。在緊急安置期間執行強制鑑定,其主要仍然是仰賴精神科專科醫師的專業判斷,確認其是否有自傷或傷人之虞,牽涉到病人是否在強制鑑定中受到公平的對待(例如,病人陳述意見表達感受的機會),其在操作上可能造成病人的負面感受,則我們仍須從程序面上調整,杜絕隱性歧視或不當對待,盡量降低病人在鑑定過程中不好的經驗。
問:刑法87條之監護處分之改正對於還有精神疾病的受刑人而言是好的修法嗎?(編按:刑法87條之監護處分之改正是指在年初時針對患有精神疾病之受刑人之監護處分的時限的修法,在修法後對於因為監護處分之期限的上限取消,使得人權團體擔憂是否會導致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受刑人就此無法重返社會,終生只能困於司法精神醫療機構中。)
答:在談論這個話題之前,我想要先釐清一個社會大眾常見的迷思。在重大刑案中,民眾往往將這些精神疾病犯罪者的行為與其精神疾病症狀連結,但同時也有民眾常常認為這些犯罪者往往會以患有精神疾病做為要求減輕刑期的藉口。此外,媒體也常常對對於有精神疾病的犯罪者的某些精神疾病特徵放大檢視,然而,在經過司法精神鑑定後,這些特徵往往不是其犯罪的主因。在這種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病人仍有不友善的氛圍下,當監護處分解除時,患有精神疾病的更生人重返社會後,若欠缺足夠良好的精神醫療照顧與社區支持,精神症狀再度惡化的風險仍然存在,並且可能對於社會安全有負面影響。然而,就人權的角度,儘管在法務部曾報告性侵害加害人強制診療期間少有超過十年,將來監護處分期間是否也有此種情況,仍在未定之天。相較於過去,現行刑法第87條不再規範監護處分的期限上限,難以避免長期監護處分之可能,的確會對於這些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權造成不良影響,這是社會安全與人身自由之間的兩難;並不是將所有的精神病患與社會隔絕就能解決問題,司法精神醫療機構總有一天會床位會用盡,這些受到汙名化的一群人也總有一天會重返社會。因此,在當今的修法方向上,保安處分執行法已放寬監護處分的執行場所,除了司法精神醫療機構外,更生人也能有比較多元的選擇,例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方案等,在未來甚至有可能加入社區支持方案,在執行監護處分過程中給予更生人更多的自由度,對於更生人的人權而言會是更好的選項。
有關病人知情同意權:
問:在臨床現場如何具體落實嚴重精神病人之知情同意權?
答:在傳統知情同意的定義上,足夠良好資訊的提供、病人有能力且正確地了解資訊並自主地作出決策,乃是有效知情同意的三大要素。某些精神疾病的病人,例如比較嚴重的失智症或思考障礙的病人而言,要同時符合上述三個要素較為困難,因為其接收資訊與思考的能力有限,需要透過精神科醫師的專業與家屬翻譯的通力協作才能確保訊息能正確地傳達,也要支持其作出自主決定。而對於CRPD的意旨而言,知情同意的內涵還包括不可以失能為理由來剝奪病人獲知資訊和表達自身意思的權利,即病人永遠有能力可以否決醫療處置,當病患表達抗拒時,醫師不應違反其意願作任何進一步的治療,這也是CRPD在醫療場域的實際操作上較困難之處。因此,在臨床現場也仰賴醫病關係的建構,當病人對醫師累積足夠的信任時,病人對於醫療處置的信賴感與疑懼下降,可使得治療過程更為順利,既確保病人的鑑健康權益,也尊重病人的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