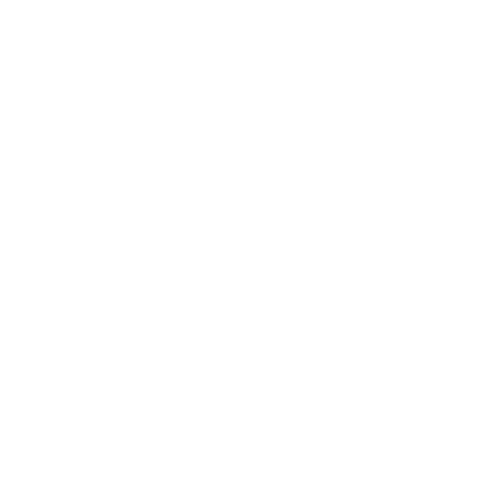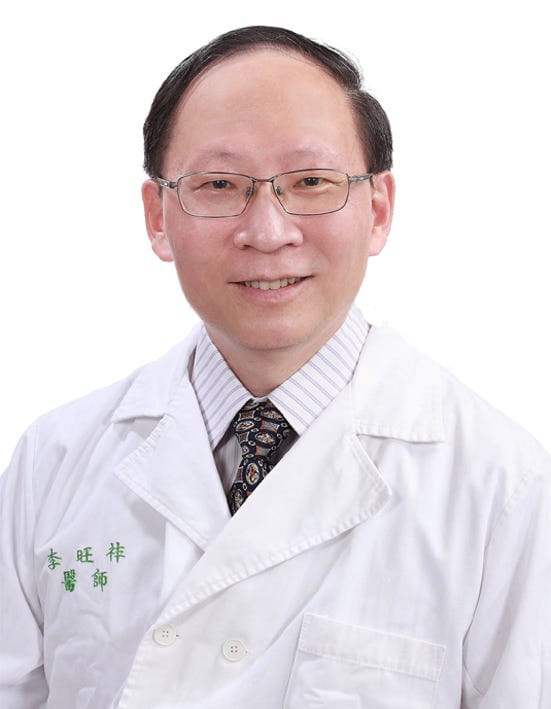傷害的折射:從巴氏量表醫療暴力事件談醫病關係的精神圖景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十九刊

本文刊於《臺大醫訊》第十九刊
撰文:b10 廖彦宥
前言:無效審判
在今年五月,台北三軍總醫院的醫生因為拒絕為不符合資格的病患開立巴氏量表,進而使家屬因為不能夠聘請工時較長且較便宜的國際移工而引發衝突,最終釀成暴力事件,而這也讓巴氏量表的存廢議題重新受到公眾的廣泛討論,而在此之外,醫療糾紛與醫療暴力的持續發生也使我們反思:為何台灣的醫病關係在近年來出現了愈來愈多的醫療衝突?而在疫情期間,台灣的醫護人員遭受了多少社會精神壓力?這些壓力的來源又是怎麼造成的?
當我們重新觀看這場醫療暴力的影片,我們可以發現醫師與病患家屬本身存在著十分尖銳的關係:當病患家屬得知自己無法透過巴氏量表的許可聘僱國際移工後,感覺到自身權益受損產生的憤怒情緒,使得他開始向醫師做出預備動粗的舉動。另一方面,醫師則以他的行為違反醫療法提出控訴,並要求他即刻停止這項行為。在基於醫療法的口頭訓斥下,似乎這場醫療衝突即將得來短暫的壓制,然而,不知道是眼神的交會,或者是來自內心不滿的衝動未得到緩解,病患家屬向醫師揮拳,所幸撲空。醫師看到此番景象,重申自身受到醫療法的保障,並且提及自身在醫療場域下的壓力,如照護病人的勞累還要遭受醫療暴力等等。這些話語似乎在家屬耳中如同情緒勒索,於是更加激怒了病患家屬的情緒。他又揮了一拳,而這次沒有揮空,直接打在了醫師的正臉上,而這也是媒體不斷傳播放大的片段。
後面的情況我們可想而知:醫師受到大眾的同情,病患家屬受到公審,公眾輿論則成為這場審判的陪審團。然而,正如過去曾經或未來即將發生的醫療暴力而言,這種審判並無法真實地消解醫療暴力,因為他們只關注醫療暴力的結果,而不考慮醫療暴力如何形成。這甚至加深了醫師與病患的鴻溝,為未來更激烈的醫療暴力誕下了可能性條件。我們應當反思:為何病患家屬會如此焦慮、甚至憤怒於無法聘請國際移工?這期間是不是有什麼制度上的問題?考慮到家務型國際移工在台灣的可悲處境,這是不是也暗示著某種排他性的國族意識?另一方面,又是什麼讓醫師被迫待在醫療法的保護傘下,而非與病患建立信任的關係?當醫師說出自身的醫療場域中所得到的壓力時,為何病患家屬無法共情?醫師在當代狀況下被迫增加了多少情緒勞動?
病患的焦慮:新自由主義的視角
如果我們從病患的角度來看,我們或許能指出這是新自由主義下的醫療化而產生的焦慮。藍佩嘉在台灣的教養場域的研究中指出,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家長竭力向教育機關爭取選擇權來為自己的小孩取得最好的教養方式。本該相互作的親職與教育機關形成了互相對立的關係。然而,這種語法遮蔽了階級關係對於選擇的影響,使得家長將自我責任化,當自身因為各種可能的階級因素而無法為小孩達成自己所認知的最佳選擇後,則將自身的錯誤選擇道德化,將之視為自己的責任,而不去反思整體結構性的問題,這形成了新自由主義下親職焦慮的來源。
而當我們將這套論述放在醫師、病患家屬與病患所構成的關係中,我們也能發現到類似的狀況正在發生:病患家屬或病患以病人自主原則為依據,要求醫療機關應該提供自己特定醫療,包括這次的巴氏量表,的權利,而不聽從在他面前醫師的評估。而若是醫療人員無法達成家屬的訴求,則醫護人員甚至會受到醫療暴力的對待,顯示出台灣社會對於醫護人員的態度已經從相互信任託付逐漸轉向一種純粹的消費者關係,他們購買的是一個商品,而非醫療。若再不成,則轉換到其他的醫療院所進行消費,直到達到病患的目的為止。我們看見了病患的自我責任化使得病患與醫療機構形成了相互對立的關係,並且將自己無法獲得自己所選擇的醫療視為自身道德上的失敗,進而感到憤怒或焦慮,卻不考慮是否應該和醫師合作,討論在治療方案上的其他可能。
新自由主義的醫療化是如何形構的?從表面上看,新自由主義無疑給個體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感,如彈性的僱用制度帶來員工流動性與短期工的增加,使得受雇者不確定感加深。其次,強調競爭力與自我功績使人們常處在高壓狀態中,這使得罹患精神疾病風險增加。再者,新自由主義導致的資本逆向分配導致貧富差距擴大,進而造成使得相對剝奪感增加,貧富矛盾逐漸尖銳。最後,跨國流動頻繁,所使得傳染病的風險大幅提高。而在社會氛圍上,風險社會的產生與專家話語的興起,使我們處在一個唯有自己信任的專家告訴我們可能面臨哪些風險,才會知道原來自己處在哪種風險環境中的時代之中。這產生了人們因過度依賴專家權威而導致脆弱性與依賴性的新人格特質,卻不考慮自身的階級狀況。
我們可以得出這些結論:從新自由主義對個人身體的責任強調與醫療化的由下而上的建構看來,透過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醫療化其實呼應了Michel Foucault所探討的權力概念,權力存在多種模態且各以不同的狀態進行對於常民的滲透與蔓延。權力因此是生產的,而非自上而下的壓迫的,對於個體而言是內在的而非外在的。醫療論述在建構上對個體重要性的強調,已使得醫療論述的要素內化至個體認知中。醫療化不再只是社會控制的壓迫形式,也是個體主動建構自身的再技術化,而這種形構最為著名的形式也就是健康生活。
我們其實可以發現,健康生活方式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是種個人階級地位之線索,這從健康餐的價格總是比一般餐點的價格還高就能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這種健康生活。Robert Crawford指出,那些強調日常生活的風險的論述,如暴露於陽光下會有皮膚癌的風險,腦瘤的產生與手機的使用有關等,引發個人的健康恐慌。甚而,當代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對於疾病的汙名化並不符合Erving Goffman的範式,是他者與自身的互動過程,而是來自於自身對於自身疾病的污名化。許多日常生活一旦被納入醫療化的檢視範圍,便會出現許多「潛在風險」,這種思考模式,他將其稱為「健康主義(Healthism)」。健康主義所推崇的正向心理學要求人們應該去思考種種正面的事物,卻忽略了病痛本身對於身體的影響,使得病患不僅無法真實地面對病痛,也無法真誠地將病痛那如自身的生命經驗中,使其成為一個純粹異質性的存在。此外,正向心理學也代表著群眾之間的自我監視,透過排除那些不正向的思維與情緒,遮蔽了資本主義的結構性不平等,也壓抑改變人們團結起來改變社會的動力。
醫師的壓力:教育社會學的比喻
而當我們回到醫療端,我們可以發現到當代的臨床醫學的高度階層化與對於統計的高度依賴是醫護人員形成壓力的主因。高度階層化能夠卻到病患可以接受一定程度上客觀且秩序化的醫療,確保每次的醫治流程趨於一致。這種一致性不僅是為了病患,同時也是為了生產更多的醫療知識:一群客觀的醫治流程是根據制定好的醫療指引產生,而對於這些醫療指引的實證,通過統計數據的分析,可以做為醫療指引的修改依據,形成社群內的自我更新。這些醫療知識的生產不僅可以鞏固醫療機構本身的權威性,並且能夠作為政治機關制定公衛政策的參考。醫師的診治過程從此不只是對於病患而言,同時也是對於整個生命政治的治理體系提供權力的來源,使機構後續的治療行為能有對身體控制的正當性。
那麼,這種體制是如何讓醫護人員產生壓力的呢?我們不妨利用教育學的視角分析:教育社會學者Michael Apple指出,教育體制的套裝化會強化教育者在教育場域的工具理性思維,因為這些教學指引使得教育的設計與執行的環節產生分裂,造成去技術化(de-skilling),剝奪了教師實踐其教育理念的空間,讓教師備感空虛。然而,教育政策制定者可以透過再技術化(re-skilling),將教師的注意力轉移到如班級管理、親師關係的互動等依賴技術所產生的學科上。我們不難發現,臨床指引的制定與新自由主義下對於醫療行為的消費主義化,對於醫護人員而言是去技術化的過程,而醫護人員試圖增加醫病溝通、進行照護相關的培力,則是再技術化的過程。而顯然地,在新自由主義下的病患與醫療機關的對立使得再技術化的過程無法產生,醫護人員不僅無法從醫病關係中得到心理上的滿足感,還需要在被病患送上法院的風險下試圖展開溝通,隱藏自身的負面情緒,強迫自身進行更多的情緒勞動。
Karasek與Theorell在對於職場社會心理壓力的研究中指出,工作者會因為失去對於工作的控制,使得工作者無法無法對於自身的行為產生價值的理解並賦予意義,因而導致厭煩與無力感。若缺乏對於工作的決策能力,將會導致工作者對於工作內容無所適從,進而失去工作的動力。因此,高工作負荷和低工作控制的組合被稱為高壓力工作,以其無法對自身的工作價值產生認同,而醫護人員便滿足這樣的條件:在高度階層化的工作環境下長期工作,並且還需要受到病患潛在的暴力衝突。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下,這種情況更為明顯:瘟疫使得醫護人員的工作量激增,然而,病患與醫師的對立關係使得溝通等再技術化無法開展,相對隨之而來的只有對於醫療體系的不信任,導致各種心理或肢體壓力在醫療場域中,透過病毒的放大使其更為顯著。
因此,醫護人員逐漸盛行起防禦性醫療:透過各種檢查來滿足病患的各種要求,並且透過各種話語的掌握使其避免受到後續的訴訟,而不去理會自身的基於病患徵狀而進行的醫療判斷。而讓我們將視角重新回到巴氏量表,即「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的依據。當我們認識到醫師在裡面所需要評估的內容後,我們可以發現其內容做為一位和病患只存在短暫的診療關係而言,不免過於苛刻:如是否能獨立沐浴、是否有大小便失禁等,醫師並不參與病患的日常生活,又如何能夠為病患做出開立巴氏量表的決定?這無疑使得醫師進入低控制的狀態,陷入不是在開立後被檢察機關提告,或者是在拒絕後遭受病患與其家屬醫療暴力的風險。巴氏量表的存在有其必要性,這不僅保障國際移工的工作權益,也避免這項資源受到濫用。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於國族主義的最後界線。然而,其開立應該依賴與長期照護相關的機構,而非醫師。
轉向:醫病關係的其他可能
透過對於病患與醫師兩端的分析,我們因此可以看到兩重的折射:病人與病人家屬希望能夠看到能夠為自己提供特定醫療服務的醫師,但卻沒有意識到自身對於健康的選擇權的追求已經造成了自身與醫療機關之間的對立,而非互助合作化解病痛的團隊。醫師希望能夠看到符合病人角色的模範病人,可以正常與其溝通,對於自身的疾病有所認知並願意理解醫師的囑咐,但卻沒有看到當代新自由主義社會下病患對疾病的自我責任化與對於治療的選擇焦慮。這兩重視角的折射構成了醫病關係的傷害性邏輯,不僅使得醫病關係無法有效進展,也使得醫病兩端陷入了壓力與焦慮之中。
縱使台灣已經開始研議在法律政策的層面上改善醫護人員的工時待遇、將護病比納入考量,台灣的醫療場域的職業社會心理危害的防治仍然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而這涉及的是整體的社會文化結構的變革,需要的是一個醫病關係相互信任的脈絡重構,一種既不是以醫師為中心,也不是以病人為中心的相互承認邏輯。
關於病人自主權與醫師診斷的平衡,台大法學院教授陳聰富在《醫療責任的形成與展開》中提出以下的觀點:「善意的父權主義並無排斥揚棄的必要。病人之自主權有賴於醫師善意的配合,始能真正實現。…病人自主權係在傳統醫病信賴關係逐漸式微之際,發展出來的概念,若醫病關係能夠重建傳統的信賴關係,則善意的父權關係對於病人而言,何懼之有。(第192頁)」這樣的方法顯然可以解決醫病關係中的第二個傷害性折射。
然而,即使是善意的父權仍然是父權,我們也不可能在理解自己有選擇權的情況下回復成過去的關係。相對地,當我們在談論疾病的自主性時,我們也需要注意到:疾病本身作為狀態將使得病人及其身體產生斷裂,使得病人意識到自身無法管控其身體,而在這種狀態下,所謂理性的個人自主也是不合時宜的:當人的各種感官受到影響而使得其知性無法正常發揮時,我們又該如何探討理性?
因此,更好的選擇是在醫療的過程中,除了治療(cure)之外,也增加關懷(care)的向度。醫護人員不僅是在治療一場疾病,同時也是在關懷身處於一場生命危機中的個人。醫護人員愈是能夠透過交談或其他行動去關懷病人,他們就愈能夠了解到病人的處境,並了解到他為何感到憤怒與無助,而不是單純地躲在醫療法的保護傘下。相對地,病人要能獲得完整的醫療,他就不能只意識到自己的治療,他也必須關懷他在這場醫病關係中的對象,即醫護人員。病人愈是能關注醫護人員的處境,他就越能夠理解醫護人員對他提供的建議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下表述出來,同時也意識到自身的選擇權在身體與心靈的分裂時是如此的空虛。透過對於彼此的相互理解與相互承認,醫病之間才終於能達到一種近似於朋友的關係:在此關係中,中心既不是醫師或病人,而是彼此對於疾病的共同體悟。